|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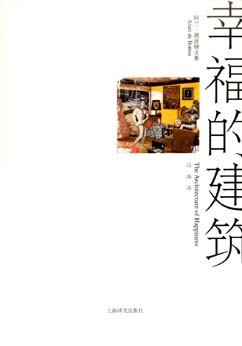 如果按照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说法,一幢理想的现代中国建筑的品质可以比之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令人倾慕的中国人的品质,我估计在普罗大众中间很难找寻到一种所谓“幸福的建筑”的看法。中国大地上正在上映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于建筑、住房和房价的战争。放眼现在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房地产战争相比:从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自焚事件,从真实反映当今房奴辛酸和奋斗历程的电视剧《蜗居》的火爆,从一个个钉子户为了维护自己的弹丸之地愤而抗法……这些事件无不与建筑和住房有关,但全都无关美好,相反倒是彰显着人与人之间残酷和绝望。这个时候读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简直觉得是一种无望的奢侈和精致的反讽,而且越看越像是一个现代版的都市童话。 如果按照英伦才子阿兰·德波顿的说法,一幢理想的现代中国建筑的品质可以比之于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令人倾慕的中国人的品质,我估计在普罗大众中间很难找寻到一种所谓“幸福的建筑”的看法。中国大地上正在上映着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关于建筑、住房和房价的战争。放眼现在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能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如火如荼的房地产战争相比:从成都女企业家唐福珍自焚事件,从真实反映当今房奴辛酸和奋斗历程的电视剧《蜗居》的火爆,从一个个钉子户为了维护自己的弹丸之地愤而抗法……这些事件无不与建筑和住房有关,但全都无关美好,相反倒是彰显着人与人之间残酷和绝望。这个时候读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简直觉得是一种无望的奢侈和精致的反讽,而且越看越像是一个现代版的都市童话。
我们首先需要一栋属于自己的房子,然后才能在其中安置自己对美的诉求。这样的一个前提所反映出的正是我们对钢筋混凝土构成的城市的一种依赖感,或者说个体对一个私密空间的向往。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公共领域的变化,公共建筑的增多逼迫着越多的人去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秘密空间的所在,因此对住房的要求首先是一种实用性的心态。从此我们能发现现代建筑处于一种矛盾的情境中,一方面,建筑总是一种实用取向的艺术,与音乐、绘画和抒情诗相反,将建筑与实用的背景分开是很困难的;但另一方面,建筑受制于文化现代性的法则,即是说,一旦建筑的实用性得到满足之后,它会极力渴望挣脱实用性的束缚,追求一种审美诉求的自主化。想想我们在拥有自己的房子之后对其做了一些什么吧,在小则几十平米大则上百平米的空间之内,我们使出浑身解数用最好的装潢装点一切,把自己的欲望尽力伸展开来,仿佛在那个小空间内,能够装下整个世界。我们在外部世界所缺失的部分仿佛能够从这个狭小的空间能重新找到似的:那个小世界中容纳下的是我们大大的梦想。
现代建筑的最大特色就是标准化、单一化。如果你想在那种整齐划一的风格中发现是否存留一丝美感的话,你只能拉近对它的观察距离,换句话说要深入到一栋建筑的肌理部分,深入到千家万户才能发现多样性的美感。德波顿在《幸福的建筑》中借助于“抽象”和“移情”解释我们在建筑中发现的美感:“我们之所以会被某物吸引,以美称之,是因为我们察觉到它包含了可以体现某些品质的浓缩形式,而这些品质正是我们个人或更宽泛地讲我们的社会所缺乏的。我们尊重那种可以带我们远离我们害怕之物并接近我们渴望之物的风格:一种包含了我们缺失的价值的合适剂量的风格。我们之所以需要艺术,首先就是因为我们几乎一直处于不平衡的危险状态中,无法在极端中寻得中庸,无法把握住人生中相对的重大极点——厌倦与激情、理智与想象、单纯与复杂、安全与危险、朴素与奢侈——间的黄金分割点。”这种分析的好玩之处在于,德波顿认为我们在现代都市生活中日益匮乏的情感缺失是因为冰冷的建筑吸收所致,因此为了改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日益淡漠和冰冷,我们可以通过改变建筑的美感重新激发生命的激情和活力,“一个国家的建筑特性就像这个国家整体的民族特性一样,是创造出来的,而不是被动地由其国土决定的。历史、文化、气候和地理都会提供一个广阔的范围以供建筑选择与之产生回应的可能的主题”。
追根溯源,现代建筑缘起一群不折不扣的理性主义观念,以对古典主义风格的建筑的反叛而崛起。现代建筑最初的时候保持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格,它延续了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的命脉,力量异常强大,足以创造出成为经典的一系列模式,而且确立了一种超越国界的风格。德波顿所谓的国际风格正是指这种现代建筑风格,但现在看这种整齐划一,跨越国界的建筑风格只能让人陷入绝望,因为这种以国际风格的名义所弃绝的正是美的多样性。而且当每个城市都几乎一样的时候,人们无法逃避这群钢筋混凝土的怪物。按照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分析,这样的建筑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现代性的面目:冰冷、理性、单一。某种程度上,德波顿对“幸福建筑”的渴求也是一种对现代性建筑群的批判:没有灵魂的容器,与环境缺乏协调,公共建筑群的壅塞、孤独和傲慢,被高耸入云的建筑的阴影遮蔽的狭小广场,人造植物和绿树给人的清新的错觉,污浊的空气……现代的城市愈加让人厌恶,怀旧成为了缅怀过去美好时光的方式,追寻虚妄幸福的重要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