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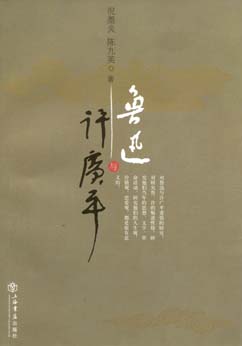 还在1991年的下半年,我写过一篇《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发表在上海的《上海滩》杂志上,不料受到意外的欢迎,竟有十几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南方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者托文汇报《笔会》的老编辑余仙藻先生来与我联系,希望我为他们再写几篇这类文章,并许以极高的稿酬。这篇文章其实我并没有用心的写,不少内容是转述许广平的回忆而成。记得上海的《报刊文摘》在摘要转载时,前面有几句摘者的话,其中说到“这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使我恍然大悟:我们过去在介绍鲁迅时,谈他的“斗争性”多,好像鲁迅在整天拍桌打凳地骂人,而他的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却谈得很少。其实,鲁迅是伟人,同时也是平凡的人,他同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怎样再有机会写写鲁迅的家庭、爱情、婚姻的生活。我以为,以连载文字的形式来写,或许可以写得真实、生动,有可读性,能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我虽然这样酝酿,但迟迟没有动笔。 还在1991年的下半年,我写过一篇《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生活》,发表在上海的《上海滩》杂志上,不料受到意外的欢迎,竟有十几家报刊全文或摘要转载。南方一家妇女杂志的编者托文汇报《笔会》的老编辑余仙藻先生来与我联系,希望我为他们再写几篇这类文章,并许以极高的稿酬。这篇文章其实我并没有用心的写,不少内容是转述许广平的回忆而成。记得上海的《报刊文摘》在摘要转载时,前面有几句摘者的话,其中说到“这里有不少鲜为人知的内容”。这使我恍然大悟:我们过去在介绍鲁迅时,谈他的“斗争性”多,好像鲁迅在整天拍桌打凳地骂人,而他的作为儿子、丈夫、父亲的“甘为孺子牛”的一面,却谈得很少。其实,鲁迅是伟人,同时也是平凡的人,他同样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从那时起,我开始思考,怎样再有机会写写鲁迅的家庭、爱情、婚姻的生活。我以为,以连载文字的形式来写,或许可以写得真实、生动,有可读性,能更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我虽然这样酝酿,但迟迟没有动笔。
直到1998年,我才从繁杂的事务中摆脱出来,于是想动手写我所设想的连载文字。这年10月,我有机会和文汇读书周报副主编刘绪源先生一起出差去西安。出差途中,我与老刘谈起我的设想,他极为鼓励。他还开玩笑说:是否打算写成鸳鸯蝴蝶派的文字?我说:我打算严肃地写,写得既有可读性,又有学术性,必须言必有据,而不采用小说家的虚构、想像和编戏剧性故事,真实地写也会有吸引力的。我托他能否探探文汇报的有关编者,是否会有连载的兴趣?他答应帮我去游说。
从西安回到上海后,我开始写《鲁迅与许广平)),到1999年3月间,断断续续写了15节。但我不再写下去了。因为哪一家报纸连载,既关系到内容安排,也关系到每节的字数。如日报和晚报,每节的字数要求不同,内容的要求也会相异。6月底的一天,我和绪源兄相会在一位朋友请客的饭店里。他让我把已写好的几节交给他,他再去给文汇报社负责连载文字的编辑看看。7月2日,我把已写好的15节给他。他于7月6日在电话中告诉我:“你的连载稿子看过了。是否就在我们周报发表?”这真是天大的好消息。
我深知文汇读书周报的发行对象是知识分子,多数读者是关心读书界信息和文史知识爱好者。已经送去的15节,老刘说不要改了。以后绪源兄一再关照:要有新材料,要有新见解,既要使一般读者读得下去,又要使圈子里的人感到有新意。他所说的“圈子里的人”就是指熟悉现代文学的人。他自己是中国现代文学专家,十分熟悉鲁迅、周作人的著作,也了解很多现代文坛掌故,许多地方他就随手作了很好的修改。有好几节的内容,我是在电话里和他商讨而定的。因而本书中融入了他大量的智慧。在最后一节发表以后,他告诉我,听到一些反映,总的说来是好的,有的内行也说有点新的东西。他说话时的语调,好像松了一口气。我深深体会到他把拙文的发表完全当作了自己的事情。
在拙文发表的过程中,我也直接或间接地不断听到褚钰泉兄、何倩兄的意见和鼓励。我感受到他们的关爱。
在拙文刚发表时,海婴先生打长途电话对我说:“你写的都是《两地书》中的内容,当心炒冷饭啊!”《两地书》中的内容是不可回避的,但还应有其他的新鲜的内容。这确是我应十分注意的。以后海婴先生来信、来电话,逐渐增加了肯定和鼓励的语句。不少内容我是在电话中或当面向他请教后才落笔的。他应我要求,翻箱倒柜地寻找老照片,还新拍摄了几张照片给我。最后他应我的一再请求,为拙作写了序。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我对他和他夫人马新云先生折腾得是够厉害的了,在此深表歉意和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