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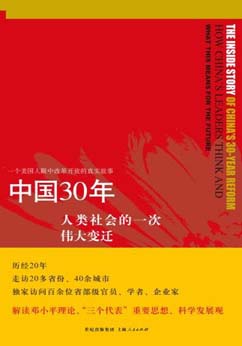 这是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在20余年的时间里,他考察了全国20多个省份,独家访问百余位省部级官员、学者和企业家。除以不同于国人的视野记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外,尤其关注领导层面的思维方式,力图向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的当代中国。其中许多资料系独家披露。 这是一个美国学者眼里的中国改革开放史,在20余年的时间里,他考察了全国20多个省份,独家访问百余位省部级官员、学者和企业家。除以不同于国人的视野记录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外,尤其关注领导层面的思维方式,力图向世界展示真实客观的当代中国。其中许多资料系独家披露。
1
2008年初,中国以2.2亿的网民数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网民人数最多的国家,而且这个数字还在继续上升。到了年中,便已经突破了2.5亿。按照目前的趋势,中国的互联网用户将会很快超过美国的总人口数。
2008年6月,胡锦涛总书记第一次通过互联网与网友交流,是在由《人民日报》经营的“人民网”的论坛里,他的这一行为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很多媒体都对胡锦涛在“人民网”与网友的在线交流给予赞誉,它们纷纷用大标题来报道此事:“胡锦涛将会更加关注网民的意见”;“胡锦涛通过互联网积极了解民意”。中国的主要门户网站之一“搜狐网”将胡锦涛称为“中国第一号网民”。
互联网为中国的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很特殊的难题。一方面,中国政府认识到,信息自由对于推动技术进步,促进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成功,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都是至关重要的。另一方面,他们自然也十分关注这种不受约束的信息传播方式可能造成的破坏性后果,即它可能包含各种各样恶意的、色情的和带有政治煽动性的信息。
因此,两难就出现了:是限制信息并延缓进步呢,还是取消限制,并承担不稳定的风险?一些人认为,为了社会稳定,应该关闭那些在政治上有破坏作用,或者有色情内容和其他不可取内容的网站,但这实在是一桩没有尽头的差事。随着接入方式、交流路径与分布式路由的不断增多,想要阻截网站的技术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了。
中国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从江泽民到胡锦涛,都非常重视互联网对于中国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中国的领导人希望尽可能地发挥互联网有助于改革开放的作用,而同时限制那些不利于稳定的因素,以便让中国成为一个有着足够高生活水平的和谐社会。
纪思道是《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也是该报原来驻北京的记者。在2008年年中的一篇文章中,他写道,“我发现开放的尺度在不断扩大。在聊天室里,对政府政策的含蓄批评很普遍。我甚至可以在《人民日报》的网站上发表尖锐的批评和不利的论断。”
2008年年中,中央宣传部部长刘云山告诉我说,到目前为止,“我们有200万个网站,8000万博客。西方还老是攻击我们管制;如果管制,怎么可能有这么多网站和博客?怎么可能有这么多人去发表他们的评论?”
刘云山部长称赞互联网,说它可以揭示真相,戳穿谣言。他以2008年早些时候发生在西藏的事件为例,“比如今年3月14日,拉萨事件发生以后,互联网就充分而又真实地反映了民意,”他说,“那也不是我们发动的。如果管制的话,也不可能有那么多人发表意见啊。”
“互联网也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刘云山认为,“互联网上也要有秩序,没有秩序不行,那会阻碍了互联网的发展。我们的法律法规并没有去控制网络,它们实际上是维持秩序的。所以在法律框架下,互联网上完全自由,包括言论自由,发表意见的自由,是一个完全自由的社会。”
2
我同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副主任蔡名照了见面,他是中国政府有关互联网事务的主要官员。我们交谈了很长时间。
蔡名照回忆起了中国互联网的历史。1994年4月20日,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胡启恒到美国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签署协议,这是中国正式接入国际互联网的开始。但是中国互联网的故事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时候。
大概在1986、1987年前后,蔡名照任新华社江苏分社副社长。当时新华社有位很有名气的老记者陆亨俊去美国采访,回来后写了一组有关“信息革命”的报告,在国内引起了轰动。那一组文章还有后来类似的一些文章,引起了中央高层领导的重视。
新华社抽调了一批非常优秀的编辑开始做信息产品,像路透社一样为企业提供信息服务。在全国,包括知识阶层、政府官员,还有新闻界,都在热切地盼望着如何跟上信息革命的步伐。“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热情拥抱信息时代的到来,”他说,“这是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受。”互联网正式进入中国时,蔡名照已担任新华社秘书长。1995年,新华社在香港的一家公司负责人到北京找他汇报,说想创办一家互联网企业。当时起的名字是国中网,域名是ccc.china.com。之后所成立的这家网站,就是现在中华网(www.china.com)的前身。
那个时候,在国际互联网界有一种共识:互联网上有很多有用的东西,但是也有很多有害的东西。如何防范这些有害的东西,是大家共同关注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