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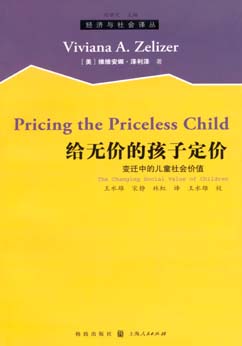 一、孩子的工具性价值与情感性价值 一、孩子的工具性价值与情感性价值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这本书适合所有声称喜欢孩子、追寻童趣并排除功利主义诉求的人阅读。当然,不排除有大部分人读完之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那份情感也是世俗而功利的,这种结论对于任何人而言都不免有些残酷。
这本书通过观察1870——1930年代美国社会对儿童价值观念的转变,提炼出了一个递进公式“有用——无用——有用”。第一个“有用”,说的是现代社会之前,无论东西方,孩子一般作为家庭(家族)劳动力的未来储备、父母养老的保险,一般农户及城市贫民家庭的小孩很小就要被设定了多种不同的家庭责任,富裕家庭的小孩尽管衣食无忧,但仍然需要体现出承继家庭家族事业的主动性、睿智、勇气。简而言之,人类几千年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小孩并没有被任何文明和社会习惯视为具体的“人”,他们只是“期货”,仅仅具备工具性价值。可以成为这种结论证据的史实是,无论在中国、欧洲还是近代的美利坚,每逢饥荒、瘟疫、战争,食物、药品、栖息地分配的人群年龄次序上,孩子通常排在有生育能力的妇女之后。
前述公式中的“无用”,指的是孩子的工具性价值削弱,而发育了其情感性价值。人们开始逐渐剥离青少年所承担的劳务责任、所长期背负的家庭责任,赋予儿童的生命以神圣意义,褒扬型的赞赏童趣、童真开始成为社会文化潮流。孩子最终成为了文化观念中,情感上神圣、经纪上无用的一种标签,未成年人保护并逐渐上升为特殊的法律规章。
第二个“有用”,则从本质上揭示出,还处在消费社会发育早期的美国20世纪上半段,被神圣化的儿童并未消失其经济角色,而是经济性从其本身转移到家庭、商业机构、学校。换而言之,儿童的价值只能通过一定的市场价格来体现,例如保险报单价、事故后较高的赔偿标准,不能生育的家庭为了领养孩子不得不付出较以往更昂贵的货币现金。并且,“有用”的重现还展现为养育子女的家庭成本激增,即无论父母多么贫困、家境怎样窘迫,未成年的孩子也很难变现自身的劳动力价值,这也是导致近年来许多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社会现代性发展相对滞后,恰是过去60年完整的经历了上述三个阶段“有用无用——有用”。《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的关注很广泛,百年前美国社会对儿童死亡的态度的改变、童工立法的斗争、儿童工作的分化过程、儿童保险的推行、儿童意外死亡的赔偿,以及儿童的领养与买卖等。不难发现,这些内容话题及其涉及的“情、理、法”、隐藏其中的金钱价值,复杂的投射于我国当前社会发展现实之中,有助于人们理性的思辨孩童对于成人(社会)的工具性价值与情感性价值。
二、生命开始变得宝贵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第一章介绍了儿童生命“神圣化”的剧变过程。维维安娜?泽利泽指出,“在20世纪,儿童悼念活动的扩大是儿童时期文化意义转变的一个表征。这种转变特别地表现在儿童情感价值新的提升之上。如果儿童的生命是神圣的,那么儿童的死亡就成了一个无法容忍的对生命的亵渎,不仅会激起父母的悲哀,而且会导致社会性的剥夺。”
这种转变是如何出现的呢?原始资本主义大生产导致的童工盛行,大量未成年人由于疾病和营养不良,呈现给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公众以悲惨的面貌,令人不寒而栗。于是,自由放任的观念第一次让位于人性,各国开始致力于降低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于是在1880年代,小儿科作为一个独立的医疗专业建立起来,而1921年——自由放任的古典保守派占据政界的最后黄金岁月里,美国国会通过了谢泼德-陶尔法案,宣布联邦政府将为婴儿和母亲的健康提供基金资助。
请注意,这种政策思路也被保留传承下来,作为对后来国家政治上是否合法的一个直观的标准,一些民族解放成立的新国家或摆脱半殖民地命运的老牌大国,之所以长期徘徊在世界舆论的底层,正是与这个领域内的错漏频出或无所作为密切相关。
作为人类20世纪最重要发明之一的汽车,从一诞生就开始扮演“儿童杀手”的角色。公共卫生的发展,使得儿童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事故死亡率自然触目惊心。更关键的是,率先使用和购买汽车的人都处于富贵阶层,而流浪在街头、无依无靠的孩子通常来自于贫寒的较低阶层,这显著的刺激了公众对“权贵杀人”的夸张性想象。在当时的美国,一个孩子遭遇车祸,公众的反应往往就如血海深仇一般,迅猛、愤慨和激烈,如果肇事者恰好不能碰上警察,往往会当场盎暴打致死。
顺理成章的,在美国社会推动了一场街头事故安全运动,资助方既有汽车公司、公共电车公司,也有保险公司,校园安全教育迅速而广泛的扩展为安全日、安全周日、安全周。数学课、艺术和戏剧课也大量加入了此类循循善诱的主题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