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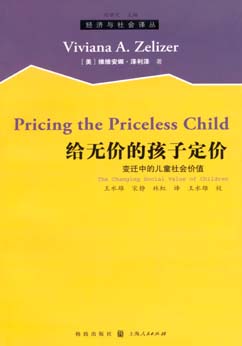 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1985年因《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而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C.Wright Mill奖。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即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 美国当代杰出的经济社会学家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A.Zelizer),主要研究领域为经济社会学,关注经济的文化与道德维度。1985年因《给无价的孩子定价》一书而获得美国社会学界的至高荣誉——C.Wright Mill奖。这本书主要写的是19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关于儿童的社会价值观念的转变过程,即经济上“无用”而情感上“无价”的孩子的出现过程。
这本书看得我心惊肉跳:仅仅在100多年前,即使是富裕人家对于死去的孩子都是草草埋葬,连个墓碑都不会留下,更不要说整个社会都把“孩子”作为纯洁,甚至圣洁的代名词了——那时候孩子首先是一种负担,其次,是家庭里的一个劳动力(工具性),就这么简单。
作者提炼出了一个递进公式“有用——无用——有用”。第一个“有用”,说的是现代社会之前,无论东西方,孩子一般都作为家庭(家族)劳动力的“未来储备”、父母养老的“保险”,一般农户及城市贫民家庭的小孩很小就被设定了多种不同的家庭责任,富裕家庭的小孩尽管衣食无忧,但仍然需要体现出承继家庭、家族事业的主动性、睿智和勇气。简而言之,人类几千年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小孩并没有被任何文明和社会习惯视为具体的“人”,他们只是“期货”,仅仅具备“工具性”价值。
前述公式中的“无用”,指的是孩子的工具性价值削弱,而发育了其“情感性”价值。人们开始逐渐剥离青少年所承担的劳务责任和长期背负的家庭责任,赋予儿童的生命以神圣意义,褒扬型的赞赏童趣、童真开始成为社会文化潮流。孩子最终成为了文化观念中,情感上“神圣”、经济上“无用”的一种标签,未成年人保护并逐渐上升为特殊的法律规章。
第二个“有用”,则从本质上揭示出还处在消费社会发育早期的美国20世纪前半段,被神圣化的儿童并未消失其经济角色,而是经济性从其本身转移到家庭、商业机构、学校。换言之,儿童的价值只能通过一定的市场价格来体现,例如保险报价、发生意外事故后得到较高的赔偿标准,不能生育的家庭为了领养孩子也不得不付出比以往更昂贵的现金。于是,人们惊奇地发现,在20世纪的领养现象中引起了巨大的“商业化”和“货币化”,生父生母和养父养母也毫不害臊地“讨价还价”。为此,作者这样指出:“一种非常明显的深刻对立被创造了出来,一边是宣称儿童是无价的情感资产的文化体系,另一边是待他们如'现金商品'的社会安排。”
作者还特别指出,19世纪末期,在美国城市劳工阶层那里,针对儿童的商业保险份额逐渐做大,并随着公共卫生、道路安全等公共产品的供给而变得越来越有利可图。一些经济学家、知识分子和政客宣扬儿童生命保险是“神圣”的开支,他们的逻辑是,既然从婴儿到未成年的孩子都开始被认为是社会的希望,必须要有一个衡量的经济标准。对此,许多儿童救助者认为,孩子的情感性价值绝不能用任何金钱来衡量,保险从业者无非利欲熏心,用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导向来造成孩童的“物化”,并可方便地上升为有钱人对贫困儿童的欺压、扼杀和剥削。更加严厉的批评背景体现为,那个时期正好有大量的新移民进入美国,美国化融合程度较差,儿童生命的圣洁很可能被其父母所侵害,理论上存在父母通过子女的死亡牟利的可能。
但保险业最终还是成功地推广了其有争议性的“产品”,并固化为美国经济社会体制的内容。这实则来源于一个苦涩的现实:美国推进公共卫生等社会福利建设步履缓慢,劳工阶层受惠微薄,大批贫困孩童不得不“违法”上岗、频繁地遭遇事故和疾病,父母们不得不担心自己的孩子会像叫花子一样下葬,这对于持有虔诚宗教信仰的广大新移民是不可接受的。虽然,父母为孩子买儿童保险被人说成是市侩而薄情,但廉价的保费支出若能换来不幸逝去孩子的体面葬礼,也算是一种聊胜于无的安慰。
“给无价的孩子定价”——题目听上去有点可怕,而这本书也确确实实横跨了儿童社会学和经济学两大领域。它是一本探讨儿童价值的书,从社会、情感和经济等各个方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孩子”两个字一说出口就可以引起人们无限温柔情意的时代,探讨儿童的所谓“工具性”与“情感性”价值似乎显得有些迂腐,但事实是,仅仅在几十年前,中国大多数家庭还是把每一个新增加的男丁视做未来的劳动力——在农村,他们甚至可以被分得土地,可以说一出生就具备了经济价值,而在当下,城市的小家庭把生育年龄一再推迟的原因之一,也恰恰是因为养育一个孩子的费用实在太昂贵了。从这些角度看,儿童,确确实实就是一个经济上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