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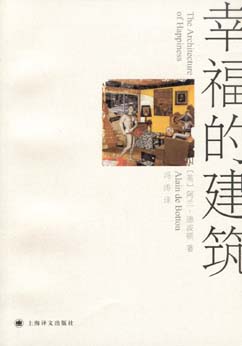 勒·柯布西耶的《东方游记》与阿兰·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都是有关建筑艺术的名著,如果你把两部书对比着阅读,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勒·柯布西耶的《东方游记》与阿兰·德波顿的《幸福的建筑》都是有关建筑艺术的名著,如果你把两部书对比着阅读,那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柯布西耶是20世纪最杰出的建筑大师,同时也是优秀的画家、城市规划专家和作家。1911年,柯布西耶开始了他为期五个月的东方旅行,历经东欧、巴尔干、土耳其、希腊和意大利。作为他的第一部著作《东方游记》便是这次旅行的记录,不仅呈现出他对大自然的迷恋、对古迹的崇拜,对东方艺术生活之美的热情赞叹,更多的是他对城市文化城市建筑的口无遮拦的评判。柯布西耶一直强调“美丽首先是由和谐,而不是由粗大、高大,或者花费的金钱数额,或者产生的舞台光芒构成的。”所以,他对走过的不和谐之地,就大刀阔斧地批判起来。这些批判的文字,刀刀见血,就像一个高超的剑客,让人闻到腥红的气息。
柯布西耶讽刺维也纳的沉闷无趣,不仅“人充满个性和贵族气的节庆,带着其全部芳香与病态”,而且“维也纳两旁的建筑很俗气,不是一种暴发户的炫耀,就是虚浮的夸张。金融家毫无情趣的摆阔氛围使这个城市黯然失色,因为它压迫人,使人不堪重负,无法快乐。”他批判布达佩斯追求不同风格的雄伟高大的公共建筑,“就像仙女身体上长的恶疮,非常迷惑人的浮华外表掩盖着无可救药的混乱。”柯布西耶把维也纳和布达佩斯批判得毫无美感,让人读起来不是很舒畅,但不可否认,却很真实地让我们看到了20世纪初建筑人文艺术里,蕴涵着的功利,给城市带来的巨大破坏性,已经到了多么让人焦虑的地步。
《幸福的建筑》这个书名与温文尔雅的英伦才子德波顿非常登对。德波顿生于1969年,90年代初开始成名。关于他的介绍,花俏得很迷人:“他博学杂收,他感受如普鲁斯特之纤毫毕现,文笔堪比蒙田之楫让雍容,趣味又如王尔德之风流蕴籍——而又不至堕入愤世嫉俗。他教我们懂得享受每天的平常岁月,教我们略过虱子,只管领略那袭华美的生命旗袍。”普鲁斯特、蒙田、王尔德,“雍容”、“风流”,这些字眼结合得非常有小资作派。而最后一句干脆就来自咱们中国的小资鼻祖张爱玲的经典名句:“生命是一袭华美的旗袍,长满了虱子”。
《幸福的建筑》的话题很有些锋芒:人为何需要建筑?为何某种美的建筑会令你愉悦?建筑与人的幸福之间到底有何关联……德波顿从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的角度对这些问题一一作了解答。可惜的是,解答完了,我就记不住一鳞半爪。其实,说起来我还是十分佩服德波顿的,我们生活中的任何话题——无论是形而上的哲学思考,还是要身体力行的旅游跋涉,他提起笔来便是洋洋洒洒一本书,比如《哲学的慰藉》,比如《旅行的艺术》。但是,德波顿毕竟不是建筑家,而只是个作家,这个局限,让他只能流于表层的表述:“建筑能够勾留住我们那些转瞬即逝、胆小羞怯的念想……”“我们的家居空间所能体现出来的情绪并不需要如何特别地甜蜜或家常。这些空间既能向我们讲述温柔,也同样能欣然地讲述阴郁”,等等诸如此类的文字,小资得优雅、精美、纯净,几乎没什么漏洞,但却明显地不疼不痒。因而,读起来,黏糊糊的,整一个不爽。
德波顿的小资艺术喜欢“略过虱子,只管领略那袭华美的生命旗袍”,迷人得很美,但却美得没了锋芒,愣让人提不起神来。而柯布西耶的剑客艺术,却直接抓住虱子,大刀阔斧得“像饱吸鲜血的大地一样腥红”,也许说不上美,经常地还很丑陋,但却张扬出了一种棱角与激情。打个通俗点的比喻,这就好像两场足球赛,一场是海水般的平静,一场是火焰般的渲泄,你说到底谁能让读者兴奋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