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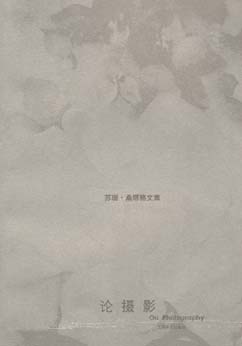 古希腊圣哲柏拉图在他的名篇《理想国》第七章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洞穴:人一生下来就在洞穴里,浑身被绑,无法动弹,后面的火光把来来往往的人的活动投射到洞壁上,洞穴里的囚徒便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柏拉图认为,这个洞穴就是我们的世界。 古希腊圣哲柏拉图在他的名篇《理想国》第七章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洞穴:人一生下来就在洞穴里,浑身被绑,无法动弹,后面的火光把来来往往的人的活动投射到洞壁上,洞穴里的囚徒便以为洞壁上晃动的影像是真实的。柏拉图认为,这个洞穴就是我们的世界。
美国著名女学者苏珊·桑塔格由此指出,人类至今还无可救药地留在柏拉图的洞穴里:“在并非真实本身而仅是真实的影像中陶醉”。桑塔格说的“真实的影像”,就是摄影呈现的世界。那么,影像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这正是桑塔格在《论摄影》这本书中要告诉我们的。
《论摄影》并不是一本摄影教科书,而是从文化的诸多层面上阐述桑塔格的影像世界理念的文集。作者明确指出,摄影成为艺术是工业化时代的产物。“摄影是随着摄影的工业化才取得其艺术地位的”。作者以其一以贯之的直率坦诚的文笔剖析了摄影师与被摄对象之间的关系:“在摄影师与其拍摄对象之间,必定要有距离。相机不能强奸,甚至不能拥有,尽管它可以假设、侵扰、闯入、歪曲、利用,以及最广泛的隐喻意义上的暗杀——所有这些活动与性方面的推撞和挤压不同,都是可以在一定距离内进行的,并带着某种超脱。”桑塔格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摄影“侵略性”的概念,包括她还论及的摄影“捕食性”问题,令人耳目一新,甚至有震惊的感觉,但稍微仔细地想一想,确是击中了要害。摄影,尤其是新闻摄影,往往是在突发的状态下,在被摄对象毫无心理准备,或者很不情愿的情况下完成的。但正是这种“侵略性”、“捕食性”,保证了摄影的实时性、新闻性、新鲜度,甚至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数二战期间,英国著名摄影家尤素福·卡什拍摄丘吉尔发怒的照片的故事。据说,卡什准备给丘吉尔拍照时,丘吉尔正叼着烟斗,神态很悠闲,无法体现这位英国二战伟人坚毅、倔强、镇静的个性。卡什灵机一动,冷不防一把夺下他的烟斗,丘吉尔刚想发火,卡什按下了快门,于是,二战史上传播最广、影响最大的一张丘吉尔肖像诞生了。但谁能想到,这幅成为战时英国人精神象征的摄影名作竟是摄影家不按常理出牌,用充满侵略性的摄影方式完成的。
工业化时代为摄影师的工作提供了社会用途,但摄影在广泛地记录社会生活、见证历史的同时,也必然产生道德、美学等多方面的问题。那么,摄影与道德究竟是怎样的关系?桑塔格对此做了十分清晰的表述:“照片不会制造道德立场,但可以强化道德立场——且可以帮助建立刚开始形成的道德立场。”诚哉斯言!如果以为摄影能确立人们的道德规范,那就像我们的古人把文章看成“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一样愚妄幼稚;但如果漠视摄影对社会生活的道德影响,也不可取。1972年,刊登于世界各大报刊的一名被淋了美军凝固汽油弹的越南女孩张开双臂,痛苦地尖叫和狂奔的照片,令世界各国的民众为之震撼。不能说这幅照片导致了美国侵略越南战争的终结,但它对反战舆论的增强、反战力量的扩大所发挥的作用,依然不可小视;同样,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青年报的摄影记者在大别山区拍摄的那位大眼睛女孩苏明娟渴望读书的照片,对推动国人投身于“希望工程”这项泽被后代的神圣事业所产生的影响,时间已经作出了很好的回答。
摄影起源于纪实的绘画。在照相发明之前,绘画承担了记录重大历史事件、描述特定年代社会风俗的使命。然而,绘画与摄影毕竟不同。摄影最大的贡献,用桑塔格的话讲,是“通过接管迄今被绘画所垄断的描绘现实的任务,把绘画解放出来,使绘画转而肩负其伟大的现代主义使命——抽象”。两者之间的区别又在哪里呢?桑塔格的阐述十分简洁、精到:“画家建构,摄影师披露。”一个源自美术的功能——美化,一个源自摄影的科学特性——讲真话的道德标准。这无疑能帮助我们准确地认识和把握两者的差异。
阅读本书,常常会为桑塔格对摄影的文化本质洞若观火的审视及其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所击节赞叹。她用一种抽丝剥茧的严密论述,一种冷静而锋利的解剖,甚至是既出人意料又合乎情理的反讽,直击事物的核心。诸如“最终,人们可能学会多用相机而少用枪支来发泄他们的侵略欲,代价是使世界更加影像泛滥”;“现在是怀旧的时代,而照片积极地推广怀旧”;“摄影师们企图改善现实的贫化感,反而增加这种贫化”,等等,警策犀利,读之有如醍醐灌顶,回味悠长。
《论摄影》虽然写于上世纪70年代,却有历久弥新、超越时空的魅力。就我们认识影像世界,尤其是数码时代的影像奥秘而言,本书无愧为“摄影界的圣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