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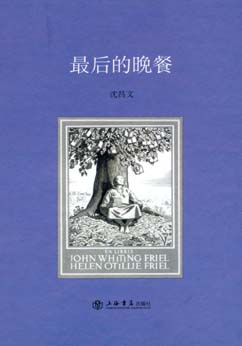 上海书店的“小三十二开硬精装”系列,最近又出了几本书人闲话式的集子:沈昌文《最后的晚餐》、《书商的旧梦》,傅月庵《生涯一蠹鱼》。 上海书店的“小三十二开硬精装”系列,最近又出了几本书人闲话式的集子:沈昌文《最后的晚餐》、《书商的旧梦》,傅月庵《生涯一蠹鱼》。
沈昌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持三联书店和《读书》,为国人奉上了一席席丰美的盛宴,至今思之,犹感神旺。“编而退则写”的这两本新书,忆述其接触的文化名人,记录其拿手的“以食会友”,也杂谈经历的事件、书籍与歌曲等,让我们得窥一些出版界的内幕秘辛,一些前贤名士的趣事佚闻。
但二书的价值除此之外,还有另一个也许为人忽略的方面,是沈昌文对编辑工作的点滴记写、感慨、思考(以及转述前辈们的言传身教)。忝为一个业余写作者,读这种名编的夫子自道,感到是很有意思的“交流”。这当中大量涉及到老《读书》之定位、文章风格等话题。关于《读书》的新一轮风波才刚消停不久,我就不摘录陈翰伯、吕叔湘等以及沈昌文自己早就提出过的好见解来“借古讽今”了,有心人自可看看,或可生“太阳底下无新事”之慨。这里只谈其中一件纯技术性的小事:阿拉伯数字与汉字之争。二十年来,大陆官方规定“出版物中的数字在绝大多数场合都必须用阿拉伯数字”,“学界对此怨声载道。”但沈昌文从一开始就在陈原的宽容下“悍然决定:《读书》不实行这办法”。而不用阿拉伯数字的代价,是不能评上某些奖项,于是沈昌文“一下狠心:《读书》杂志索性不参加任何评奖。后来,更发展为: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不参加评奖”,也不管没有奖项可能关乎“单位处境乃至个人升迁”。
这确实够“悍然”,对汉字够义气。相应地,我留意到“晚餐”一书插附的名家手迹中,有一份吕叔湘交给《读书》的文章手稿,里面原本偶有阿拉伯数字,都被用笔改为汉字。这修改,应该是《读书》编辑坚决执行沈昌文的意见;而作为插图,则无意中呼应了“旧梦”一书中那篇令人肃然起敬的《阿拉伯数码之灾》。
但编辑修改作者文章,也应谨慎为之。迫于时势的没办法——如沈昌文经手出版的《宽容》、《情爱论》、《第三次浪潮》等,在八十年代反响极大,他本人一直引以为荣,只是几本书中一些段落内容当时被他“把关”删减掉,令他至今痛心惭愧,忏悔罪孽——除却这类政治因素的删改,更常见的文字改动,便是编者与作者间一个不大不小的永恒话题了。沈昌文转引张爱玲的《编辑之痒》一文,谈到文章字句被编辑改错了:“尽责的编者看着眼生就觉得不妥,也许礼貌地归于笔误,迳予改正。在我却是偶有佳句,得而复失,就像心口戳了一刀。”张爱玲的感受,该是很多作者的共同体验。沈昌文的意见是:编辑确要尽责,但应当承认编辑总的来说不及作者,要“自愧不如”一些,不应不打招呼就乱改。可是,“编辑之自满,也许大陆这里又胜于世界别处”,沈昌文的谦卑姿态并不能成为“行规”。写这篇《自愧不如》后几年,他又写了篇《一个错字》,讲的是他的《阁楼人语》一书,有处说毛泽东的名言是“不刊之论”,结果被出版社编辑“看着眼生”,改成意思完全相反的“不堪之论”印出来,马上引起别人关注。读到这里,我不禁坏笑兼苦笑:这样的编辑老行尊自己出书都吃到这种苦头了,真是一个好玩的讽刺。
以上两个细节问题,也是我所在意的。我发表文章、特别是出书时,曾专门就数字尽量使用汉字与编辑“互动”过,至于字词被编辑乱改而引致“心口戳刀”与苦笑,也不时发生(所幸真正改得好的编辑亦遇过不少)。读了沈昌文这两本书,感到即使不论他在三联书店和《读书》惠泽深远的业绩,光是拒绝阿拉伯数字的勇气,对待作者文章的谦卑,都是值得致敬和怀念的。能有所为有所不为,能把握哪些当为哪些不当为,这才是一个真正的编辑家。当然,这也是普适意义上的做人的高标准了,以是沈昌文更为难得。
沈昌文的“晚餐”、“旧梦”主要内容是“人”,见出作者这个人以及笔下一群人,由人而及书;来自台湾的傅月庵的“蠹鱼”,则主要是谈书,由书而及人。傅月庵也是编辑,但更是书痴,他之所以选择这个工作,就因为“整天看书又有钱拿”。读读写写,乐在其中的“生涯一蠹鱼”,结集了这册关于中西文学、古今文人的读书随笔——有点儿近于叶灵凤《读书随笔》的风格,只是在古典雅致与西洋风味中,显得鲜活与浅近些。内容以张潮《幽梦影》之“读诸集宜春”、“读史宜夏”、“读诸子宜秋”、“读经宜冬”来分四季之辑,也让我欣赏;虽然各辑的文章并不严谨对应(就像他的读写往往随性散漫),但有那么一点意思一份情味,也就好了。
书中有不少可赏可喜的典故与见解,摘抄一段,以见一斑:
他谈美国女作家Lynne Schwartz的《读书毁了我》,指出这书名译得不好,原文不是“毁我一生”那么严重,“大概更接近中文‘葬送’一词。明的如龚自珍所谓‘美人经卷葬年华’,隐的如陆游诗云‘万卷诗书消永日’,庶几近乎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