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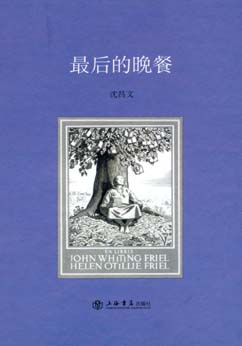 京城几位颇懂趣味的老叟中,沈昌文先生以会吃著称。有一次听到王学泰先生说,现在懂吃的人多,会吃的人少。这话有些费解,细想起来自有道理。“懂吃”与“会吃”在研究饮食文化的专家眼里,当有所区别。大抵“懂吃”包括懂得择菜、懂得下厨亲手烹制,而“会吃”的要义,则多在品味这些细致活儿的佳妙,吃出感觉来。长沙官话说“懂味”,所指范围甚广,意思并不在饮食上,不过最初亦当从狭义的饮食口味发展出来,大有懂得理会妙处的意思。其实京城里因善馔而为人称道当属王世襄先生,畅安老人烧得一手好菜,买菜择菜做菜全由自己包下,当算作“吃家”。而沈昌文先生“吃性”与“吃情”皆佳,当然不忘对此事有所记录,其新著《最后的晚餐》里《王老教我做菜》一文,说的就是这件事。 京城几位颇懂趣味的老叟中,沈昌文先生以会吃著称。有一次听到王学泰先生说,现在懂吃的人多,会吃的人少。这话有些费解,细想起来自有道理。“懂吃”与“会吃”在研究饮食文化的专家眼里,当有所区别。大抵“懂吃”包括懂得择菜、懂得下厨亲手烹制,而“会吃”的要义,则多在品味这些细致活儿的佳妙,吃出感觉来。长沙官话说“懂味”,所指范围甚广,意思并不在饮食上,不过最初亦当从狭义的饮食口味发展出来,大有懂得理会妙处的意思。其实京城里因善馔而为人称道当属王世襄先生,畅安老人烧得一手好菜,买菜择菜做菜全由自己包下,当算作“吃家”。而沈昌文先生“吃性”与“吃情”皆佳,当然不忘对此事有所记录,其新著《最后的晚餐》里《王老教我做菜》一文,说的就是这件事。
沈公写文章喜谈往事,新出版《书商的旧梦》与《最后的晚餐》二书,皆为沈公近些年闲适生活的随笔,所做文章起于本世纪初年,止于2005年,记录其“老有所感”,内容多为记事怀人,言多涉险,直抒胸臆。文辞洒脱如常,间或亦有其他类如书评等等。文中颇多掌故,可作书话小品来读,总有些滋味。尤其“文学版图与文化厨房”一词颇妙,单咀嚼字面便耐人寻味。作者自言:“职业是编书匠,工作就是同文人学者说短论长,于是饭馆成为最好的聚会地方。近十多年来,喜欢同朋友说的话是:咱们哪天找地方叙叙!这‘叙叙’,不是去中山公园,也不是逛天安门,而一定是去某家餐馆大快朵颐。”话虽这么说,但沈公这二册书里,谈吃的文章并不多,与坊间传言不甚符合,足可知他是擅馔不擅厨,趣味与才情都从“懂吃懂味”上作了交代,讲究的是饭食的品味。
按说沈公是上海人,谈老北京的话题自不会多,信手可写的还是吃食。“我素好饮食,特爱上小馆。”沈公此话颇能看出他平日多喜地方特色口味,在《吃遍中国》文中,沈公道出吃的经验:“老食客目前在北京可讲究的,是吃真正的地道各地风味。于是摸索出一条捷径:去各省市办事处的饭馆吃饭。”坊间关于沈公的传说,一曰他退休后不甘寂寞,每天都必往三联书店走一遭,可见他对三联的旧情深厚。一曰他胸前挂着电子记事本,京城特色餐馆及其地方菜式皆存其内,每日中午必在餐馆用膳已成他的风格。又一曰他下午必到三联书店二楼咖啡廊小坐,喝咖啡闲聊,因此想要访他,往此处多可获得。因此沈公晚年生活被注解为:三联、美食、咖啡,释作“文化、品味、闲适”也算贴切。这里不妨引知堂语:“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于生活而言,讲究的正是闲情逸致。
《书商的旧梦》收文四十三篇,每篇千余字,全书统共约八万字,精细可读。全书文章所写皆作者任职三联书店及《读书》杂志期间之闻见与编辑经历,随其所咏,往事风云舒卷纸上。作者自喻“书商”,因而笔底文字轻松,吟风唤雨,洒脱自然。“我这辈子都是做牛式的出版:听话、恭顺,不敢越雷池一步。”读他的文字感受,知他是遇事豁达忍让、为人开朗又自得其乐的好好先生,寻常并不为人事纷纭所恼,但遇到强制性指令,免不了也会作些抗争,这种随和中包含原则,是所谓绵里藏针的性格。书中《阿拉伯数码之灾》一篇,直指出版物中数字用法的规定“实在要不得”,于是“一下狠心:《读书》杂志索性不参加任何评奖。后来,更发展为:三联书店的出版物不参加评奖”。读此甚感快慰,见出作者性情。他行文的风格多快语人生,《罪孽之一》说:“曾经说过大话:房龙的作品是我在大陆改革开放后首先引进的。总觉得,这好歹是功劳一桩,可以称道一下。”颇有些自赏神情,显得憨态稚拙,是通常老年人的顽童模样,不妨作掌故视之。
《最后的晚餐》前部分文章所怀念的皆为作者前辈,所记人物费孝通、汪道涵、李慎之、柯灵、荒芜、吕叔湘、金克木、许国璋、陈翰伯、陈原、冯亦代,多为作者主编《读书》时工作相关,寄托作者的个人情感。此类文章二十四篇,其中尤以写陈原先生文字居多,前后有八篇,正可见出作者情深所系,感慨唏嘘都为多年相戚与共。书中文字婉转有致,多有耿直之言,大可一赞。书中后部分谈饮食,得文十四篇,篇篇有趣。《酒中的糟糠之妻》:“你不妨信步走到街头,找个小酒店,喝它一二瓶‘普京’,或者‘小二’。纵然没有朋友在一起,听听周边的人的言论,也许有某几个老人正在讲齐化门的往事,一些年轻朋友在议论娘儿们的新潮”等等,信笔恣肆,意味深长。到了他这般年纪尚憨态可掬,复淘气可爱,可算为京城一道嘴边风景。全书共收文三十八篇,九万余字,与前面所谈《书商的旧梦》一书相仿佛,似乎“旧梦”与“晚餐”可为姊妹配,倒也玲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