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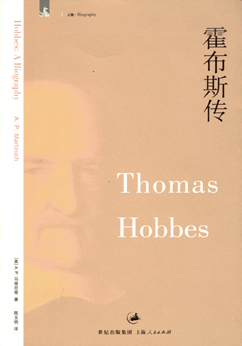 我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开始对霍布斯做正式研究的。我的博士论文写完之后不久,我所在委员会的同人伊莎贝尔·汉格兰德(Isabel Hungerland) 问我是否愿意翻译霍布斯的《论物体》的第一部分。伊莎贝尔要写一篇霍布斯有关‘涵义”与“意义”的理论的评论,翻译《论物体》算是个配套的工作;按照原来的安排,这个工作本应由另外一个人去做,结果原来的计划流产了,于是伊莎贝尔就要我帮忙,因为她知道我对拉丁文和语言哲学比较熟悉。其实,我只是对哲学史有所了解,对霍布斯并不熟悉。但是出版商已经在等着伊莎贝尔的翻译,我也知道助理教授们所面临的出版压力,所以我接受了这一任务。最后,我的有关翻译和评论在1981年出版了,汉格兰德和乔治·维克(George Vick)还为它写了一篇颇长的导言。 我是出于功利的目的才开始对霍布斯做正式研究的。我的博士论文写完之后不久,我所在委员会的同人伊莎贝尔·汉格兰德(Isabel Hungerland) 问我是否愿意翻译霍布斯的《论物体》的第一部分。伊莎贝尔要写一篇霍布斯有关‘涵义”与“意义”的理论的评论,翻译《论物体》算是个配套的工作;按照原来的安排,这个工作本应由另外一个人去做,结果原来的计划流产了,于是伊莎贝尔就要我帮忙,因为她知道我对拉丁文和语言哲学比较熟悉。其实,我只是对哲学史有所了解,对霍布斯并不熟悉。但是出版商已经在等着伊莎贝尔的翻译,我也知道助理教授们所面临的出版压力,所以我接受了这一任务。最后,我的有关翻译和评论在1981年出版了,汉格兰德和乔治·维克(George Vick)还为它写了一篇颇长的导言。
一开始,我从逻辑学和语言哲学的角度看霍布斯,觉得他的著作很一般,并无特别的新意和说服力,因此,我以为我跟他的交道就算打完了。几年后,我被逼给研究生们开一次有关霍布斯的讨论课——天可怜见,就因为我出版过一本有关霍布斯的书,我竟被当成了研究霍布斯的专家。我并不看好这件差事,不过我知道《利维坦》被人视为一本伟大的著作,而我并未认真读过它。没想到,仔细读过之后,我居然很喜欢这本书,讨论课也上得不错。所以我决定在介绍宗教哲学时加入霍布斯,并且又开了一次有关霍布斯的讨论课。但是,在阅读霍布斯时,那些通行的二手著作让我很不满意——它们似乎并不符合原文和历史背景。我读得越多,对霍布斯的兴趣就越浓,也越发觉得我自己对霍布斯的解读比通行的解读都要好。最后,这项研究的成果就是《(利维坦)中的两个上帝:托马斯·霍布斯的宗教和政治思想》(1992)。除了他在政治哲学上的理论目标以外,我认为霍布斯还想在正统基督教教义和现代科学之间进行调和,以证明真正的基督教并非政治不稳定因素。
我认为他的计划注定要失败,但我相信他从未意识到这一点。从他一生的生活方式可以看出,他是一个虔诚的英国国教会信徒。
我现在研究霍布斯已经是出于一种纯粹的智识上的乐趣,而不是出于狭隘的功利目的。对他的哲学、生活和历史背景研究得越多,我就越为之倾倒。
让我高兴的是,现在霍布斯已经不再只是哲学家们的研究对象了。近来出版的有关霍布斯的优秀著作大多出自研究政治和科学的历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之手。我从中受益匪浅。
我要感谢特伦斯·莫尔(Terence Moore)于1994年邀请我做这项研究。
作为“议会史研究”的编辑,安德鲁·斯拉士(Andrew Thrush)博士慨允我查阅第一代和第二代德文郡伯爵传记的手稿。伦敦雅典娜图书馆俱乐部(the Athenaeum club)的图书馆馆长助理凯·沃尔特斯(Kay Walters)慨允我翻阅查尔斯·布劳恩特((Marles Blount)的习字簿。在写这本书的不同阶段,我的部分或全部原稿经下面各位看过:
乔·安·卡森(Jo Ann Carson),格里高利·迪肯森(Gregory Dickenson),玛格丽特·丢厄克森( Margaret Duerkson),马修·埃文斯(Matthew Evans),劳伊德·盖提斯第三(Loyd GattisⅢ),肯奇·胡克斯特拉(Kinch Hoekstra),大卫·约翰斯顿(David Johnston),科瑞·朱(Cory Juhl),弗莱德·孔兹(Fred Kronz),布赖恩·列维克(Brian Levack),莱斯利·马蒂尼奇(Leslie Martinich),马克斯·罗森克朗茨(Max Rosenkrantz)和乔治·莱特(George Wr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