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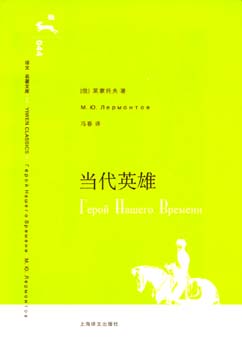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继普希金之后,俄国保守势力又杀害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当时他还未满二十七岁,已是公认的普希金继承者,俄罗斯第二位大诗人。 一八四一年七月十五日,继普希金之后,俄国保守势力又杀害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诗人——莱蒙托夫,当时他还未满二十七岁,已是公认的普希金继承者,俄罗斯第二位大诗人。
莱蒙托夫的创作时期主要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这是俄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十二月党人起义被镇压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进一步加强了他的反动统治。他成立了专门镇压进步活动的第三厅,颁布了书刊检查条例。进步贵族遭到打击,一切自由思想的表现、抗议沙皇暴政的举动都遭到镇压。整个俄罗斯成了一座监狱,到处是死刑、流放、苦役和设好圈套的杀害。革命运动处于低潮。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俄国革命就像一团埋藏在地底下的烈火在那里重新生成、酝酿、积聚,新的革命力量在人民内部逐渐生长,虽然它还没有显露出来,但那不满,忧愤,试图反叛、对抗的情绪却始终是存在着的。莱蒙托夫的创作就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点。
米哈伊尔·尤里耶维奇·莱蒙托夫一八一四年十月十五日生于莫斯科。父亲尤里·莱蒙托夫生于一个家道中落的贵族家庭,曾在军中服务,后以上尉军衔退职,定居在图拉省克罗波托夫卡村。母亲玛丽亚出身名门斯托雷平家族,但在莱蒙托夫未满三岁时便已病故。莱蒙托夫由外祖母伊丽莎白抚养,童年在外祖母的庄园奔萨省塔尔哈内村度过。他从小亲眼目睹农奴的贫困生活,接触到俄罗斯民歌、民间舞蹈、民间传说,听到不少有关一八一二年卫国战争的故事,这对他未来的创作都大有裨益。
一八二七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迁居莫斯科,一八二八年进莫斯科大学附设的贵族寄宿中学就读,同年开始诗歌创作。一八三〇年莱蒙托夫考入莫斯科大学伦理政治系。当时莫斯科大学足全国精神生活的中心,别林斯基、赫尔岑、斯坦凯维奇、奥加辽夫等都曾在这里学习。进步学生组成各种小组,热烈地研究政治、哲学和文学问题,这种气氛对莱蒙托夫无疑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时期他写了长诗《卡勒》、《伊斯梅尔-贝》和《乞丐》、《天使》、《帆》等抒情诗,其中《一八三一年六月十一日》是具有代表性的一篇。高尔基后来指出,在莱蒙托夫这一时期的诗歌里,已经开始响亮地传出一种在普希金的诗歌里几乎听不到的调子,“这种调子就是(对)事业的热望,积极参与生活的热望。(对)事业的热望,有力量而无用武之地的人的苦闷——这是那些年头人们所共有的特征”。
一八三二年莱蒙托夫随外祖母到了彼得堡,考入近卫军骑兵士官学校。两年后莱蒙托夫在骑兵士官学校毕业,被派到彼得堡近郊皇村近卫军骠骑兵团服役。
一八三六年莱蒙托夫在彼得堡开始写作中篇小说《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小说暴露了贵族社会的腐朽与专横,对上流社会外的小人物寄予深切的同情。小说第一次出现彼乔林的形象,他和《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一样,是个近卫军军官、贵族社交界的代表。他们身上有许多共同的东西——对上流社会的抗议,对在那特定社会条件下出现的“多余人”身上的缺点的自我揭露和批判,因而《里戈夫斯卡娅公爵夫人》中的彼乔林成了未来《当代英雄》中的彼乔林的草图,后者正是前者的发展,并且最终构成了一个更加完整丰满的形象。
一八三七年二月八日,普希金在和法国流亡分子丹特士的决斗中受了重伤,两天后与世长辞。这个消息震动了全俄国。一向把普希金视为自己精神上的主宰的莱蒙托夫立即拍案而起,写了悲愤交加的《诗人之死》,向沙皇及其帮凶——维护俄国专制制度的反动集团发出愤怒的声讨。《诗人之死》立即以手抄本形式传遍彼得堡。这首诗代表了一切善良正直人士的心声,获得了广泛的共鸣,莱蒙托夫的诗名也随着这首诗的传播而誉满文坛。可是这首诗也给莱蒙托夫带来了厄运,它引起宫廷的震怒,莱蒙托夫终于被流放到高加索,到尼日哥罗德龙骑兵团服役。
以《诗人之死》为标志,莱蒙托夫的创作进入了成熟阶段,在进步人士中被看作普希金的继承人,从而受到热烈的欢迎。
一八三九年至一八四〇年莱蒙托夫在《祖国纪事》杂志上发表了小说《贝拉》、《塔曼》和《宿命论者》。一八四〇年五月莱蒙托夫将这几篇小说同未曾发表的《马克西姆·马克西梅奇》、《梅丽公爵小姐》合在一起发表,这便是著名的长篇小说《当代英雄》,它是莱蒙托夫现实主义创作的最高成就。
《当代英雄》的作者并不是想描写一个我国读者一般概念中的英雄人物,它在本书中应理解为一种“代表人物”,某一时期的“中心人物”或“众所瞩目的人物”,时代的一种典型。作者在本书序言中明明白白地指出了这一点。莱蒙托夫说:……当代英雄“确实是一幅肖像,不过不是某一个人的肖像。这幅肖像是由我们整整一代人身上发展到极点的恶习构成的”,作者“不过是想描绘一下他所理解的当代人,以此自娱,只是这种人他见得太多了……”作者明确地指出,他所写的是“整整一代人”,这种人“太多了” ,因而书中的丰人公是一种典型,这种人具有普遍性,是社会中广泛存在的,是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普遍的时代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