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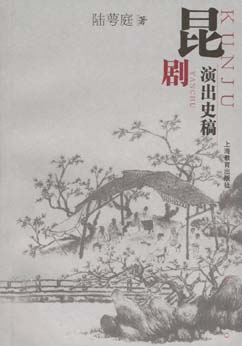 陆萼庭先生的遗著《昆剧演出史稿》今出新版,出版社以特邀责任编辑相约。我与著者不敢妄称深交,“平生风义兼师友”却是实情,因而只感到义不容辞,不暇虑及能否胜任,就接受下来。能为亡友遗著尽绵力,固然是一种荣幸,但也是一件憾事,遇到疑难问题无从征询,不能获得面聆教益之乐了。 陆萼庭先生的遗著《昆剧演出史稿》今出新版,出版社以特邀责任编辑相约。我与著者不敢妄称深交,“平生风义兼师友”却是实情,因而只感到义不容辞,不暇虑及能否胜任,就接受下来。能为亡友遗著尽绵力,固然是一种荣幸,但也是一件憾事,遇到疑难问题无从征询,不能获得面聆教益之乐了。
现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第三个版本。最早的版本在1980年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印行,其后著者又有创获,增补了约5万字,于2002年由台北一家出版社出版繁体字版,这次是用著者生前在修订版原稿上作了校改的自校本付排,底本几乎每页都有多处校正,足见用心之劳、用力之勤。作为特邀责任编辑,我所做的工作主要是拾遗补缺:从底本上检出偶有失校未改的字词;尽可能找到某些引用原书核对引文;发现体例上前后互异的地方改从一律。诚然,未安之处、失检之字恐怕还有,只能有待于读者指谬了。
本书是演出史著作,采用旧籍材料富赡,引文中通假字较多,一般不作改易,今仍其旧;出现异体字,则改用正字。遇到应简化的字,自当遵从,而人名(如洪舁)、专名(如舁平署)仍依原写;“齿句”字本已简化为“出”,但考虑到“《牡丹亭》一出”谓出现,“散出”指戏,“出出出色”言诸折戏尽皆出色,倘若全用一个“出”字易滋歧义,为区别计,把“一出戏”之类的“出”都改成“韵”,以避免与“出现”、“出色”的“出”同字异解,未作简化处理;另,书中“馀”字,曾一度简化为“余”,后两字并存,尊从作者习惯,仍作“馀”。这颇有“自作主张”之嫌,责我、谅我,己无法听取著者的意见了。
著者溘逝,已逾半载。赵景深先生在二十多年前写的序文中说:“这部《昆剧演出史稿》是一种探索,甚至也可以说是一种创举。”现今由我接手作修订本的责编,极个别处还须代庖,难免惴惴不安。虽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又乌可得乎。倘有违背原意之处,其过在我,有愧于著者之旧谊,有负于出版社之付托,这里就先行告罪了。
编校既毕,谨志数言,并寄追思。
王尔龄 2005年5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