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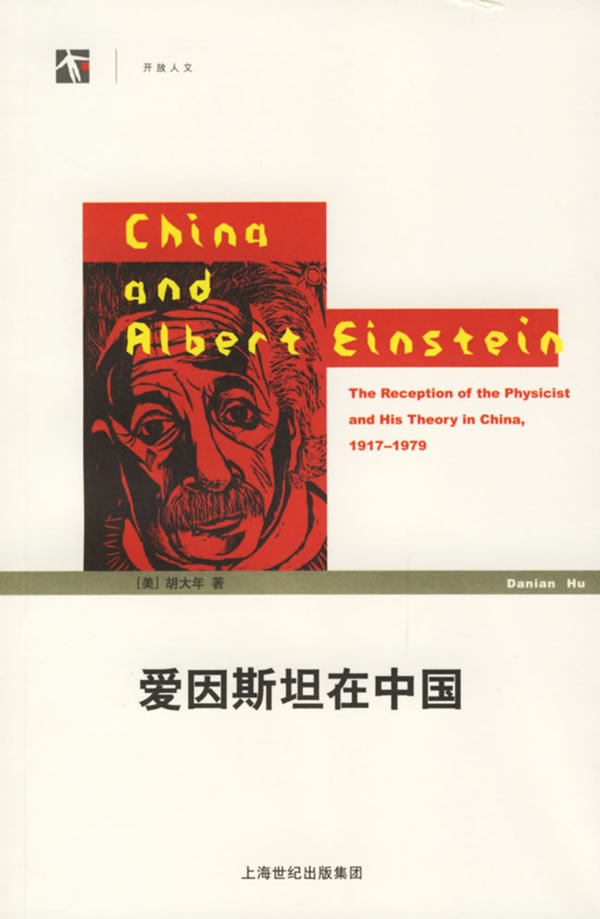 2002年8月18日,下午1点。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外面,成百上千的“追星族”排起了约300米的长队,长长的队伍竟然围着巨大的会议中心绕起了圈。 2002年8月18日,下午1点。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外面,成百上千的“追星族”排起了约300米的长队,长长的队伍竟然围着巨大的会议中心绕起了圈。
他们在等什么?歌星演唱会?重大体育赛事?都不是。他们提前两个小时来排队,为的是占个好位子,听一场关于“M理论”的科学演讲。“M理论”是一种新的大统一理论,演讲者是霍金(Stephen W.Hawking),杰出的英国理论物理学家和广义相对论专家,人称“活着的爱因斯坦”。
为了参加一次国际弦理论会议,霍金来到了北京。他的来访在中国的首都掀起了一场“科学风暴”:2200多人涌入会议厅去听他的演讲——《膜的新奇世界》。演讲的2000多张免费门票在一周之内就发放一空;有些拿到票的人企图趁机牟利,竟以每张1000元的天价私自兜售。全市最大的书店设有专柜,展销8部由霍金所著或介绍其生平的书籍,每天销量超过200本。中国国家主席会见了霍金并赞扬他对科学和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抵京之前,霍金访问了杭州,在这个美丽的邻近上海的南方城市,他也引起了公众极大的兴趣。
“霍金热”不由得让我们想起1922年中国人准备迎接爱因斯坦访华时的“相对论热”。由于霍金的声望是基于他成功地发展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而人们又常以爱因斯坦来衡量他的伟大,因此,这两个事件之间存在许多明显的相似之处也就不令人惊奇了。事实上,有必要把霍金现象当作中国接纳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历史的一部分来看待,而这段历史正是本书的主题。
相对论于“五四文化运动”期间(1917—1921)传入中国,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思想革命时期。“五四文化运动”激起了中国民众对西方科学的广泛兴趣,这为接纳相对论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于是,相对论被迅速地接受并广为传播开来,爱因斯坦则作为科学界的英雄和革命者而闻名。接受相对论是中国现代物理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这一成就的基础,是20世纪20—30年代中国物理学教育与研究成功地实行了体制化和职业化。到了1940年代,爱因斯坦和相对论基本上已从普通公众的视野中消失了。在经历了战争与革命之后,当两者重新受到公众注意时,这位物理学家和他的理论却由于从苏联进口的批判意见而被充满敌意的政治气氛所包围。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这种敌意在1960年代中期愈演愈烈,并于“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达到高潮。直到1979年,中国政府才正式地对这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及其工作作出较全面和公允的评价。
本书调查了相对论传入中国的过程和原因;通过考察一系列相关中国物理学家的生平,探讨了中国接纳相对论过程的特点;并对1917—1979年中国公众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反应作了仔细的审查与分析。基于对已发表和未公开的原始史料的研究,本书论证了日本对相对论传入中国的重要影响。此外,本书认为,中国缺乏经典物理学的研究和教育这一历史传统背景对接受相对论有关键性的影响,它帮助中国知识界在1920和1930年代迅速而无异议地接纳了相对论。最后,本书还揭示了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干涉,引导公众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采取了日益轻蔑的态度,并最终导致了“文革”期间有组织的批判运动。虽然本书仅仅集中考察了理论物理学的一个分支,但它作为一个范例,体现了20世纪中国基础理论科学的生存斗争,以及自然科学与教条主义哲学之间的冲突。
本书分为5章,第1章综述了17世纪至19世纪西方物理学逐渐传入中国的历程,其东渐之物理内容构成了中国接纳相对论的科学基础与条件。第2章调查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传入中国的过程和原因,以及相对论的介绍与中国其他更广泛的思想发展之间的联系。第3章考察了6位有代表性的中国物理学家的职业生涯,以鉴别中国接纳相对论时的特征。第4章讨论了爱因斯坦的形象在1920—1965年这几十年间的变迁,这种变迁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中国的科学与科学家社会地位的跌荡起伏。最后一章研究了“文化大革命”期间针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运动,以说明中国的科学发展是如何受到教条主义哲学“指导”的影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