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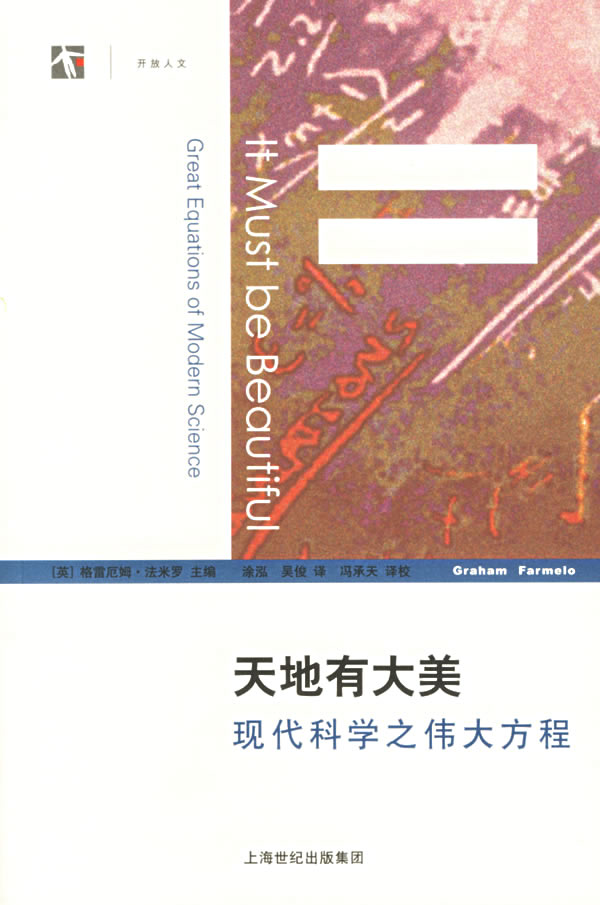 □江晓原 ■刘兵 □江晓原 ■刘兵
□古语有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如果仿此句型,是不是可以说“天地之大美曰方程”?不管怎么说,此书(原名《它肯定是美的——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的中译名定为《天地有大美》,确实相当精彩。
当年霍金的出版商曾告诉他,在《时间简史》中每引入一个方程,该书的销售量就会减少一半。当然,后来《时间简史》异乎寻常地畅销,霍金就在新版中删去了这段话。但是毫无疑问,方程是令许多读者头痛的东西。对一般文科学者来说,科学著作中的那一个个方程,就是一个个喷射着机枪子弹的碉堡啊。
也许有些心高气傲的文科学者听了这个比喻不太服气,那我们先来回顾一则轶事:1909年,哲学家安东·汤姆森——他那时还是大物理学家尼耳斯·玻尔的表姐夫,在收到玻尔寄赠给他的一本物理学著作之后,给玻尔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感谢信,信的开头说:“亲爱的尼耳斯,多谢你寄来你的大作;我读它直到我碰到第一个方程——不幸它在第2页上就出现了。”当然汤姆森是不打算再往下读了。
回顾汤姆森的信和当年霍金的出版商的危言耸听,对这本《天地有大美》来说是饶有趣味的。如果放一个方程就会使书的销量减半,那这本讨论11个方程的书,销量必定要趋于零了。而一本书专门谈“伟大方程”,那不是要让读者学习黄继光吗?
■你说的黄继光(抗美援朝战争中用胸口堵住敌军碉堡机枪眼的中国志愿军战士),对于今天的青年读者来说,恐怕已成僻典了。
我想,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讲科普书中引入公式会使其销售量剧减,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我想这也是被科普出版实践反复检验过的一种说法。但一般的规律用在个例上,有时可能就不那么恰切了。其二,这本书恰恰是选择了一个人们普遍承认的科普难点——方程——来切入,这就很有些艺高人胆大的味道了,更何况,此书还占有着另外一个在科普书中不很常见的主题,即科学之美。这些新颖之处,加上总会有一些读者也想进一步了解科学中的方程这种涉及数学的问题,因此,它还应该是会有一定的市场的。有句俗话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问题只是在于,此书虽然在标题(原标题)中明确地点出了科学之美(注意,科学之美还不等同于自然之美,因为科学理论只是由科学家提出的对自然的解释之一),书的中文译名中更像你注意到的,以“大美”(这倒是地道的中国文化里的概念)为要点,但与我经常看到的其他一些讨论科学与艺术、科学与美的书籍不同,此书似乎也还没有真正深入地对科学与美这样的问题进行透彻的分析。你觉得是不是这样呢?
□确实是这样。此书的主题并非讨论科学与美,它的主题其实就是它的副标题:现代科学之伟大方程。要搞科学就得和方程打交道。一门学问,只有当它可以用方程来进行数学描述和计算时,才算真正进入“精密科学”之列。而那些科学史上最伟大的方程——据作者认为也就是11个而已,则每个都有一大堆前世今生的故事。此书由11位西方科学家合作撰写,每人一章,阐述一个伟大方程的来龙去脉,它的演变,它在物理学上的意义,以及它可以适用的范围等。这样就构成了一部别出心裁的精密科学专题史。
■我注意到你在最后一句话中,用了一个限定性的说法,即“精密”科学专题史。这里“精密”两字甚为重要。之所以讲此限定重要,是因为,这种大量依赖数学语言来表达的科学,只是一类后来才发展起来的科学,因为其后来才发展,所以又经常为人们作为科学发展的样板,以至于形成了只有能够应用数学的科学才是成熟的科学这样的说法。
我们当然应该承认,在科学发展的这一支中,曾经取得了重要的成就,是科学史发展中的一个新的阶段。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此类型的科学之外,也还存在着其他类型的,不是那么高度依赖于数学的科学。对于早在精密科学出现之前的其他传统的科学,我们也不应该就因其缺乏数学而予以贬低。按照这种观点,才是一种多元化的科学图景。当然,这样说,也并不排斥和否定精密科学自身和了解它的重要性,而要更为深入些地了解,《天地有大美》这样以重要方程为切入点的书就是很理想的读物了。
□其实“精密”地讲,我上面关于本书是“精密科学专题史”的说法,准确程度也只有7/11——因为书中最后讨论的四个方程,就不再是精密定量的方程了。最后四章讨论的,正是你所说的“不是那么高度依赖于数学的科学”,依次是地外文明、进化、生物、环境问题,无法像前面讨论的那些物理学问题那样用数学工具进行精密的定量描述。
比较令我感兴趣的是第8章“天空中的明镜:德雷克方程”。在这样一本书中,在这样11个方程中,竟会有德雷克方程入选,恐怕不是那些保守正统的科学家愿意接受的。这一章中详细讨论了人类探索外星文明的种种方案和努力,以及各种相关的理论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