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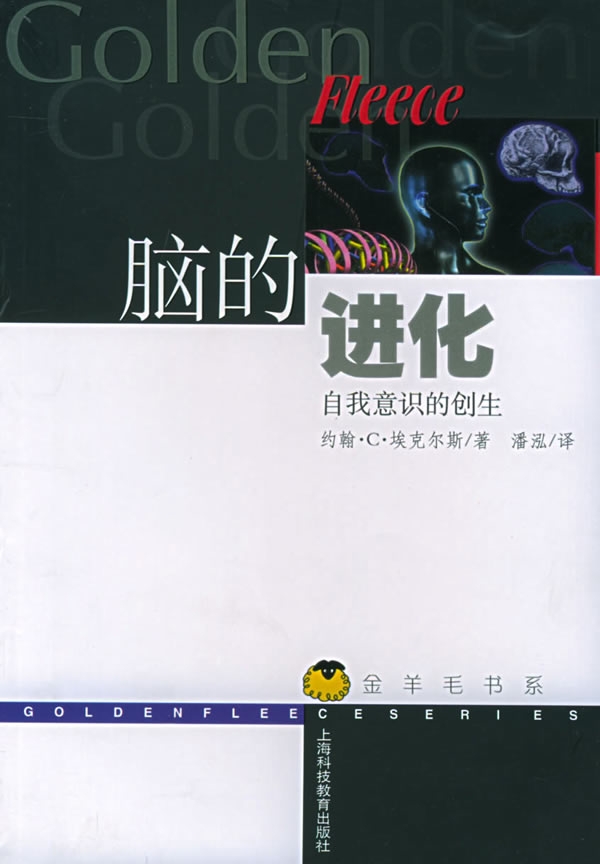 康德的这一名言脍炙人口: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想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绝对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支撑道德的根基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恰恰是对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因果律的反叛和违背。如,水往低处流,是遵循因果律而动;但人往高处走,则是人凭借自由意志做出的自愿抉择。但康德也许不会料到,随着科学的步步深入,人们在窥探大脑奥秘的同时,还试图为人类道德的出现寻找生理机制。近读《脑的进化》一书,就感受到了这一激动人心的进展。本书出自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之手,作者因对神经元之间突触机制的研究而与人共享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康德的这一名言脍炙人口:有两种东西我们愈经常愈反复思想时,它们就给人灌注了时时更新、有加无已的惊赞和敬畏之情: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在康德看来,我们心中的道德律绝对不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支撑道德的根基是自由意志,而自由意志恰恰是对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因果律的反叛和违背。如,水往低处流,是遵循因果律而动;但人往高处走,则是人凭借自由意志做出的自愿抉择。但康德也许不会料到,随着科学的步步深入,人们在窥探大脑奥秘的同时,还试图为人类道德的出现寻找生理机制。近读《脑的进化》一书,就感受到了这一激动人心的进展。本书出自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埃克尔斯之手,作者因对神经元之间突触机制的研究而与人共享1963年的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
正如书名所表明的,作者是紧扣进化这一主线来讨论人类大脑种种特质的出现过程。先来看大脑边缘系统,其重要组成部分是杏仁核的两个亚核团,分别位于边缘系统的正中内侧部和皮层-基底外侧部。实验表明,若对正中部杏仁核施加刺激,会引发不可自控的狂暴;但对外侧部杏仁核施加刺激,则引发难以抑制的愉悦感。这些情绪的产生与杏仁核分泌的生化物质有关:去甲肾上腺素和多巴胺与好斗、自我刺激有关;而5-羟色胺则导致松驰和睡眠。更有意思的现象是,在从人到猿的进化过程中,正中部的杏仁核保持在较低水平;而外侧部杏仁核则有相当大的增长。结论不言而喻:相比于动物,人类逐步享受了更多的愉悦感,同时更多地摆脱了好斗和狂暴的情绪。这一结论也与珍·古道尔对黑猩猩的野外观察相一致,古道尔发现在黑猩猩群体中存在着大量的暴力争斗行为。这就是说,在人之上升为人的过程中,我们确实在远离兽性,而逐渐享受到爱意与和平带来的宁静和愉悦。不过问题的另一面却是,令人产生欣快愉悦感的部位也正是毒品附着的地方,难怪各地的人群都能设法找到某种令人上瘾的植物以满足非生存所需,而野外生活的动物则对此一无所知。此外,人类也不可能完全摆脱正中部杏仁核产生的情绪体验,因为勇气和冒险行为都需要一定程度的挑衅进取(即好斗)精神作为支撑。在此意义上,让世界充满爱也许是一种难以企及的境界?
随着好斗暴力行为在人类生活中的逐渐淡化,一种崭新的特质开始出现:那就是同情心。休谟曾经说过,同情心是一种高贵的情感。野外生活的灵长类根本没有同情心,好斗霸道才能争得地盘和地位,进而为自身带来进食和交配方面的优先权。但人类的进化则走上了不同的道路。考古学上的证据表明,有一具六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的骨架,它出生时就是残疾,随后又受伤多次,但却活了至少40年,若没有部落里其他人的照顾,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由此可以判定,人类最早的同情心出现于六万年前。在作者看来,同情心是利它主义行为得以产生的根由。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与道金斯、威尔逊等社会生物学家的看法有所不同。在后者看来,社会性昆虫表现出来的舍己行为,如工蜂牺牲自己来成全蜂王和群体的利益,就是利它主义的表现。但在本书作者看来,这样的本能行为应该被称作是“伪利它主义”。真正的利它主义必须要有“意图”作为基础,亦即预知自己的行动是在为他人谋利。显然,出自于“意图”的利它行为只能见之于人类,且因同情心使然。
毋庸讳言,人类智力进化的顶峰也许就是自我意识的开端。有证据表明,黑猩猩能认出镜子里的自我(表现为对着镜子挪去脸上的颜色标记),这是对自我的初级意识。正如生物学家杜布赞斯基所说,自知是人类的根本特征之一,但自知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阴暗面:害怕、焦虑和对死亡的自知。不过在我看来,正是上述所谓的阴暗面,构成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最有影响的推动力。自我意识的出现也就意味着个体意识到有一个恒常自我的存在,这显然需要有个体记忆的连续性作为保证,而其物质基础就源于大脑。如此看来,躯体的每一器官都能进行移植,包括如今正在走俏的“换脸术”,但大脑移植是万万做不得的。而大脑几乎有无数种不同的神经活动模式,它们又是如何整合成为一个完整的自我意识的呢?作者提出的一个假说认为,具有自我意识的心智并不只是被动地参与神经活动,而是主动进行搜索,按照心智特有的兴趣、动机将大脑不同区域读出的结果融合在一起,从而维护个体意识的完整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