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己亥岁尾到庚子春夏,受疫情的影响,与许多人一样,陈振濂也一直“宅”在家中,期间,他潜心学术,埋首案卷,致力于书法“美育”的学术研究。过去三年时断时续的写作,在这时得以快速编撰成形,并最终付诸出版,成为这本包含了“知识篇”“图像篇”“学理篇”和100多件高清作品图片的《书法美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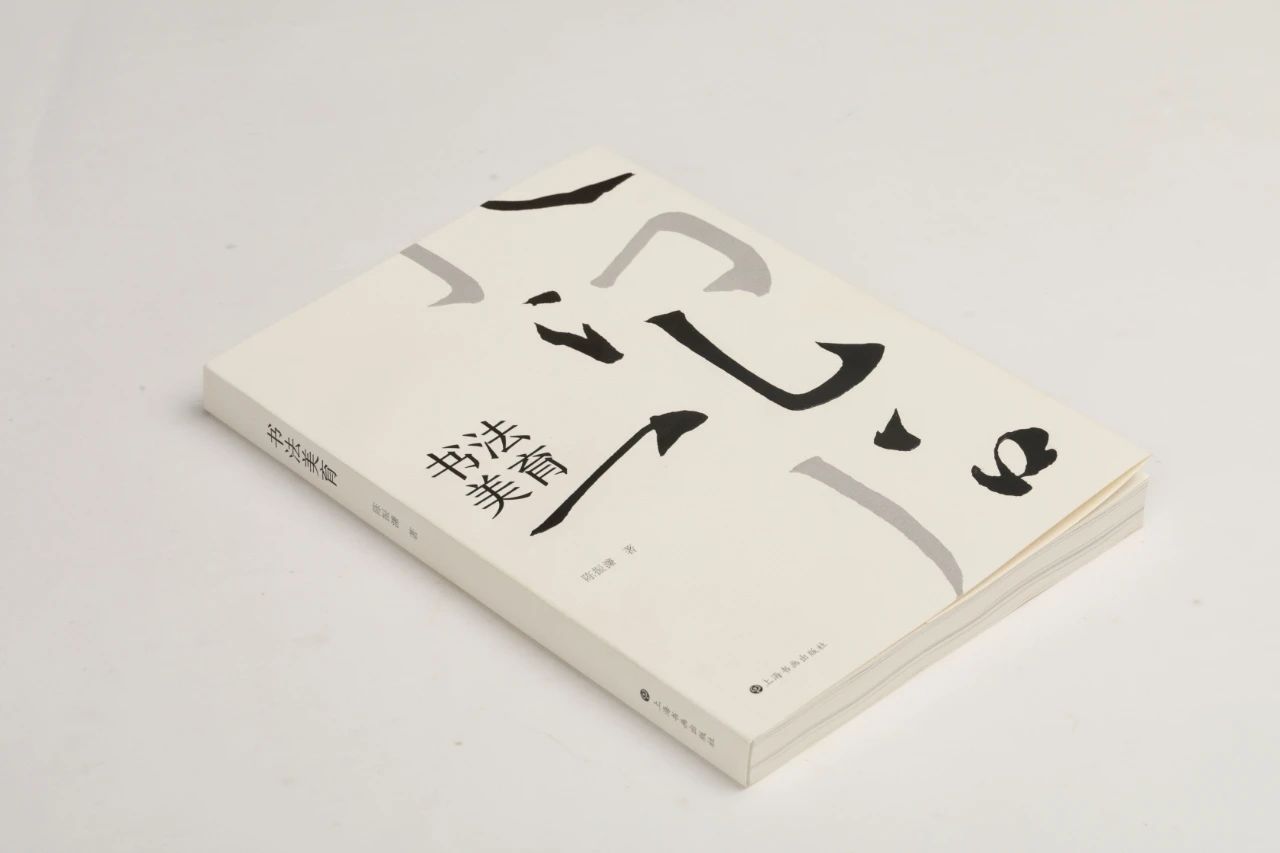
《书法美育》
陈振濂 著
上海书画出版社
书法从古代几千年走来,美感无处不在,讨论审美的经典言论也无处不在。自近代尤其是这四十年来,依靠“展厅文化”的外部生存环境的刺激、逼迫与催化而获得转型,已然彻底成为独立的艺术门类。但说是艺术,貌似至高无上,还被捧为“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却在社会公众的“美育”方面显得迟钝麻木、缺少起码的建树。
即使是一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甚至是一个大学文科教授、一个领导干部、一个科技专家、一个公司管理层,虽然他们本身都有各自的文化素养和职业积累,但书法的“美盲”几乎是一个普遍现象。对遍布社会各阶层的哗众取宠且俗气的书法,扭捏作态搔首弄姿的书法,江湖杂耍的书法,不厌其烦地津津乐道或迷茫不置可否,乃是今天的“书法美盲症候群”的通例。低如写字则太低,不足挂齿,高若创作又太高,高不可攀,而居于中间的“关键大多数”,作为书法艺术受众的最大群体,其对书法审美把握的感悟力、判断力,在当代书法领域中反而是最“缺位”的。
正是基于这一判断和认知,以陈振濂为代表的一群学者才大声疾呼,当务之急是要大力提倡书法美育,补上当代书法教育各层次分布中最缺乏的这个短板。
在《书法美育》中,陈振濂从在中国美术学院和浙江大学几十年致力于高等书法教育经验和思考出发,就书法美育的相关问题做出了最新的研究。
他认为,美育的立场,肯定不是写(毛笔)字的立场,它不针对文化技能和社会应用。美育的立场,肯定也不是高端的艺术创作实践,那本该是少数精英天才的事。美育的立场,不需要掌握炉火纯青、出类拔萃的笔法技巧,而只需要有一定程度的实践体验即可。美育的立场,也不承担在书法领域创造历史,推进艺术创新的时代责任,而只是为社会大众、广大非专业的观众、爱好者、痴迷者提供精神食粮, 使他们可以有适当的实际练习以扩展体验,但更需要的是他们的系统知识和对作品的感受力。对经典如数家珍,对笔墨形式技巧能感同身受、娓娓道来,是一个懂行的旁观者,精通专业的受众,思接千载又鞭辟入里的评论家和观赏家。在目前中国书法界中,多的是平庸的写字匠和天马行空、目空一切的“艺术大师”,最缺乏的,正是懂行的、理性的书法美解读者、实践推动者和体验者,还有优秀的观众和评论家。他们的存在,本来应该占书法领域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但在现在却反过来,也许连百分之二十都没有。倡导书法美育,其理由大率如此。
针对广大民众的书法“美育”能力的培养,陈振濂认为,对古代名碑法帖的经典传统之理解,及作为其根基的审美观察、分析、表现能力培养的意义,应该远远大于实用的点画撇捺技术练习的意义。因为对一个面向社会大众的“书法美育”课的目标设立而言,培养一个三流书法家, 远远不如培养一百位懂行的又有一定实践经验的书法欣赏家,对全民的文化素质提升更有价值。
而对于能力的培养,不是通过单纯的理论说教、概念清理即可获得的,对于一个书法初学者而言,直接的方法是借助经典法帖,因为它们是最可把握的艺术对象。当然,没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没有掌握到与名碑法帖关系最密切的“人”即名家大师的知识系统,看经典法帖也只能是浮光掠影、浅尝辄止、雾里看花。因此,他在书中通过100幅古代书法名作的分析,建立起一个关于艺术、关于书法的基本认知框架,提出书法艺术的整体概念,以欣赏、认识、观察名品为出发点,取得感性经验, 取得专业发言权和共同讨论问题的能力。
“我以为:‘美育’的倡导,是一个时代的书法责任。”陈振濂说。
陈振濂,1981年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1993年任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2000年调任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兼艺术学系主任、艺术学院院长、浙江大学中国艺术研究所所长、浙江大学书画艺术院院长,中国美院与浙江大学双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浙江省文联副主席、西泠印社副社长兼秘书长、中国国家画院书法篆刻院副院长。为国家级专家并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