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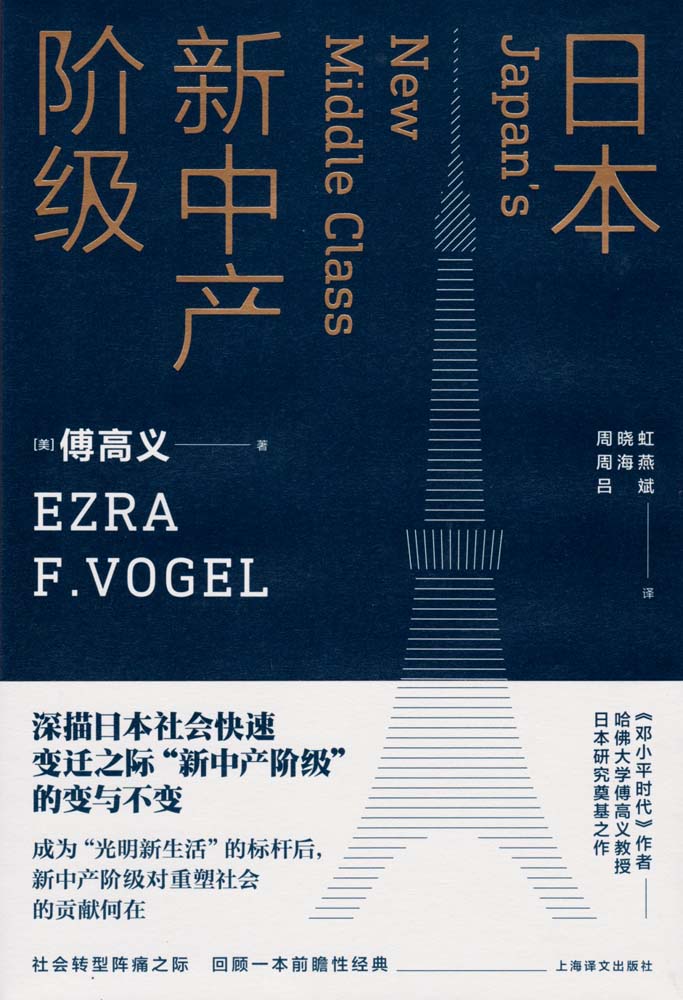 “被中产”,这是时下热门的网络用语之一。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新书首发分享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去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全球最多,但为何很多中国人不愿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认同感从何而来? “被中产”,这是时下热门的网络用语之一。在由上海译文出版社主办的《日本新中产阶级》新书首发分享会上,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李春玲抛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去年发布的《全球财富报告》显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全球最多,但为何很多中国人不愿承认自己是“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认同感从何而来?
新中产阶级,新在何处?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有哈佛“中国先生”之称、曾撰写《邓小平时代》的傅高义在1963年发表的日本研究奠基之作,中译本今年5月首次在中国大陆出版,目前首印2万册已基本发售一空。傅高义特为中国读者撰写新序,称“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在他看来,“近来许多中国家庭已经步入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他们中的一些人尤为关注日本中产阶级的现代生活方式,在文化的诸多面向上如何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影响。”
1958年至1960年,傅高义举家迁至日本东京,对东京视角的M町展开田野调查,因而《日本新中产阶级》的观察与分析细致入微。此后,傅高义夫妇一直坚持对研究对象的跟踪随访,研究成果跨越30年。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傅高义描绘了这样一个族群:二战后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取代了老中产阶级,带动了家庭、经济与文化的变革。新中产阶级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
新中产阶级新在何处?傅高义认为,此处之 “新”,并非刚刚形成的意思,而是对应“老中产阶级”即独立小业主和地主群体,指的是在大公司与政府部门工作的白领雇员,他在书中称这一族群为“工薪族”。《日本新中产阶级》简体中文版译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指出,老中产阶级的特点一是占有生产资料,二是可能自己也会从事一些体力劳动。随着后工业社会发展,新中产阶级产生了,他们包括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经理阶层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三类人群。
中产阶级到底如何界定?周晓虹认为应该有四个纬度,除了收入、教育、职业,还有认同。在中国,“中产阶级”的认同感之所以比较低,有历史的意识形态原因,也在于过去对中产阶级的主要参照体系是欧美国家,“美国中产阶级的标配是一套大房子加两到三辆车,在今天的中国大城市比如上海这样的地方,是比较难实现的。从这个角度来说,傅高义所写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于今天的中国更为贴切,这也是50多年后,这本书能够引起中国读者强烈反响的地方。”
中产阶级为何焦虑?有何任务?
在对日本新中产阶级持续不断地观察后,傅高义夫妇得出结论,新中产阶级成功的兴奋正在为某些焦虑所取代。中文版《日本新中产阶级》以该书英文版50周年纪念版(2013年)为底本,收录了苏珊娜·霍尔·沃格尔所写的《超越成功:三十年后的M町》。在这一章节最后,苏珊娜写道,“现在, M町的家庭乃至日本总体上已经达成目标,人们想知道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富裕和商业化一旦实现,就失去了其作为目标的吸引力,而令人瞩目的新目标又尚未出现。如同年轻人通过极为重要的大学入学考试后不免迷茫, M町的父母并不清楚成功之后将会怎样。他们继续努力地履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成功的兴奋已然消退,某些情况下空虚似乎开始袭来。他们期盼找到新活动、新关系、新乐趣和新意义。他们步履辉煌地走过顺畅的成功之路,正在寻找更加宏大的目标。”
在《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文版面世后,其中《“地狱”般的日本入学考试》等章节被广泛讨论,书中谈及的新中产阶级职场环境、收入结构、消费理念、社区关系、家庭分工、育儿焦虑、价值观、心理诉求等,都让很多中国读者有“感同身受”之感。有读者表示,“傅高义可能并没想到,自己的著作不仅架起了一座西方世界理解日本社会的桥梁,还在若干年后引起了中国读者的诸多共鸣,让他们知道,自己不孤独也不特殊,自己当下所经历的,60年前的日本人可能也经历过。”也有读者认为,“这本书是一块晶莹的琥珀,但并非一块指南针。你可以通过这本书清晰地看到战后日本新中产阶级的生活实录,但若说对当下中国的工薪族有什么指导意义,书中涉及有限,值得深入探讨。一本出版于半个多世纪前的日本研究专著能够引起中国读者尤其是年轻人的广泛关注,这本身就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
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卢汉龙提出,傅高义这本著作的价值在于提示当下的中国社会,如何认识和定义“中产阶级”,不仅是从职业形态、收入水平、教育程度等可捕捉的量化标准,更关键的是要研究在生产力发展方面,对今天的中国社会起至关重要的稳定器作用的群体到底是什么样的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