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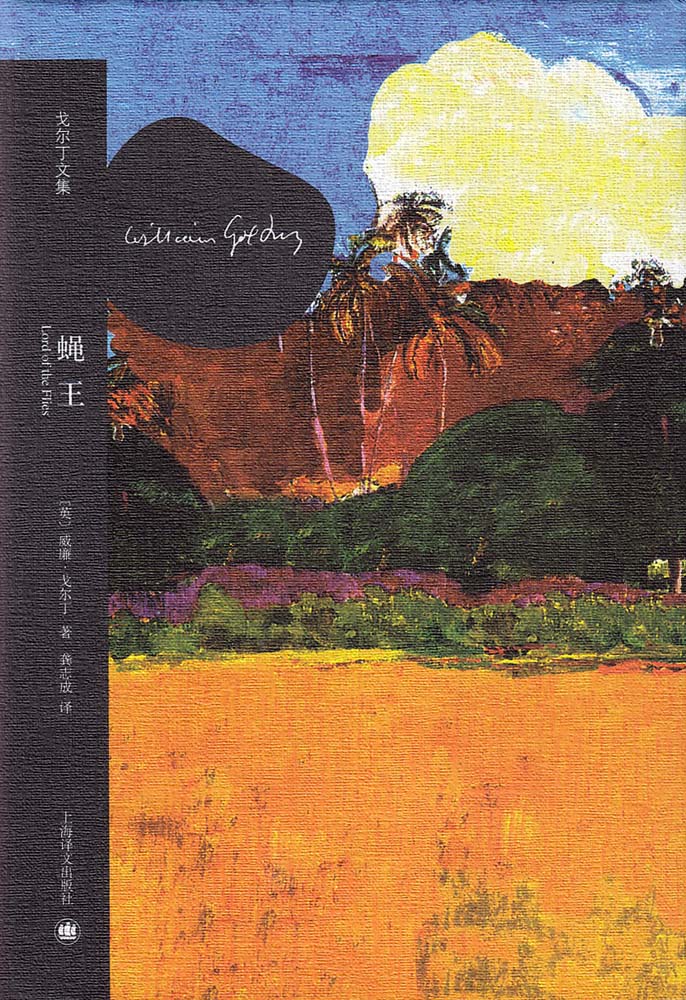 在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情节场景触目惊心的当下,重读《蝇王》,便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更现实的关怀。 在校园欺凌事件时有发生、情节场景触目惊心的当下,重读《蝇王》,便有了更深刻的感受、更现实的关怀。
英国现代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威廉·戈尔丁在《蝇王》中,构建了一个人性的实验场,逼真的描写几乎让人们相信,如果没有外来力量的介入,这个小小的封闭实验场将变成一个真实的丛林社会,只需足够的时间。
这正如校园欺凌,是一个逐渐演变的过程,如果得不到干预,欺凌行为就会变本加厉。
有序转为无序
在《蝇王》的题序中,戈尔丁这样写道:“野蛮的核战争把孩子们带到了孤岛上,但这群孩子却重现了使他们落到这种处境的历史全过程,归根结底不是什么外来的怪物,而是人本身把乐园变成了屠场。”
乐园是如何一步步变成屠场的?
小说虚构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一架飞机带着一群男孩从英国本土飞向南方疏散,途中,飞机被击落,孩子们乘坐的飞机落到了一座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
岛上有充足的淡水、丰盛的食物、湛蓝的海水和绵长的沙滩,如同伊甸园一般。
起初,孩子们以幼稚的民主形式集结在一起。这时的他们,身上还带着文明社会的习惯和印痕,还能够按照文明社会的理性和秩序来运转他们的“小社会”。在他们自发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拉尔夫被选为领袖,他规定,无论大孩子还是小孩子,都有权发言,但需要手持海螺;当手持海螺者在发言时,其他人不可以打断。
但好景不长,有序很快转为无序。孩子们分为两派,明争暗斗。失去了文明世界的理性和秩序、没有了纲纪和规则、没有了互助和合作,“蝇王”出现了。孩子们互相残杀,失去理智,堕落成嗜血的“野兽”。
“蝇王”即苍蝇之王,源自希伯来语“Ba alzebub”,在《圣经》中,被称为“万恶之首”。小说中,蝇王最直接的意象代表是“坏孩子”杰克用来“祭祀野兽”的野猪头。它在高温潮湿的环境下,被无数苍蝇叮咬,散发出阵阵恶臭,极端恶心和恐怖。它一边连接着孩子们无法战胜的自然神秘主义,一边连接着孩子们因恐怖而被激发的兽性。
设定都有深意
故事并不复杂。乍一看,似乎是荒岛历险故事和乌托邦故事的变种。但显然,《蝇王》不止于此,不然,戈尔丁也不可能凭借这部小说而摘得诺贝尔文学奖。
这是一本哲理小说,借孩子的天真探讨人性的恶。抽象的哲理命题被具体化,赋予引人入胜的故事和激动人心的争斗场面,人物、场景、意象、细节等的设定都深具象征意义。
拉尔夫是书中的主角,手持海螺,是理智与民主的象征。他有强烈的责任感,主张孩子们按照文明的原则行事,强调集体性和秩序。在拉尔夫眼里,规则和秩序是被救的基础。他把孩子们聚集到一起,搭帐篷,分配任务,试图建立一个民主、文明的“社会”。
但大多数孩子想去打猎、玩耍,当他们认为有怪兽存在时,内心的惧怕与暴力倾向被杰克唤醒。而此时,作为首领的拉尔夫,因为软弱而不能说服孩子们,甚至不能将孩子们继续聚拢在自己身边。最终,他未能把这个孤岛上的群体引向光明,不仅眼睁睁地看着“猪崽子”被杀,自己也被追得无处可逃。最终获救时,拉尔夫为岛上的生活和孩子们人性中的野蛮和恶而哭泣。
“猪崽子”是一个出身低微、患有严重哮喘病而无法从事体力劳动的戴眼镜的胖子,爱思考问题,这个形象让我们想到了知识分子。他的眼镜是唯一在物质上对他人有用的东西,因为眼镜可以聚光生火。“猪崽子”是科学精神的代言人,他相信科学,时常给拉尔夫提建议,提醒拉尔夫用螺号号召孩子们,当其他孩子被野兽吓怕时,他坚信野兽不存在。虽然他的好多建议没有被采纳,但是他不曾放弃。最后,他被杰克的帮凶罗杰用巨石残害。“猪崽子”是抱着海螺死的,至死他都坚信“海螺在谁手里,谁才能发言”。但最终海螺还是碎了,“猪崽子”是专制社会中知识分子命运的缩影:在一个文明不断遭受破坏的社会里,理智和智慧多么的苍白无力。
西蒙有着非凡的洞察力和正直的人格,其他孩子群起群居,他则喜欢自然独处,冥思苦想。在戈尔丁的笔下,西蒙犹如基督教的先知。他时常同“蝇王”对话,也同自己内心深处的原始冲动对话。他的自觉认识最终赋予他崇高的道德良知,这是其他孩子所不能比拟的。他谙熟人类内心的黑暗,同时认识到同伴的恐惧,实际上是对深藏在他们心中的罪恶和死亡的一种本能的抵制和反抗。
孩子们害怕怪兽和蝇王,西蒙是唯一一个认识到怪兽是飞行员尸体的人。为了证明自己的判断,在一个恶劣天气里,他独自一人去丛林深处探个究竟,但在归途中被残忍杀害。孩子们将西蒙当成了怪兽,隐喻着此时的孩子们自己已经成为了怪兽。
书中有一段西蒙与蝇王的意识对白,剖析了人性的黑暗,也预示这位先知的可悲命运。事实上,人群中确实存在着无数个像西蒙这样的先觉者,在历史上,他们也大都落得悲惨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