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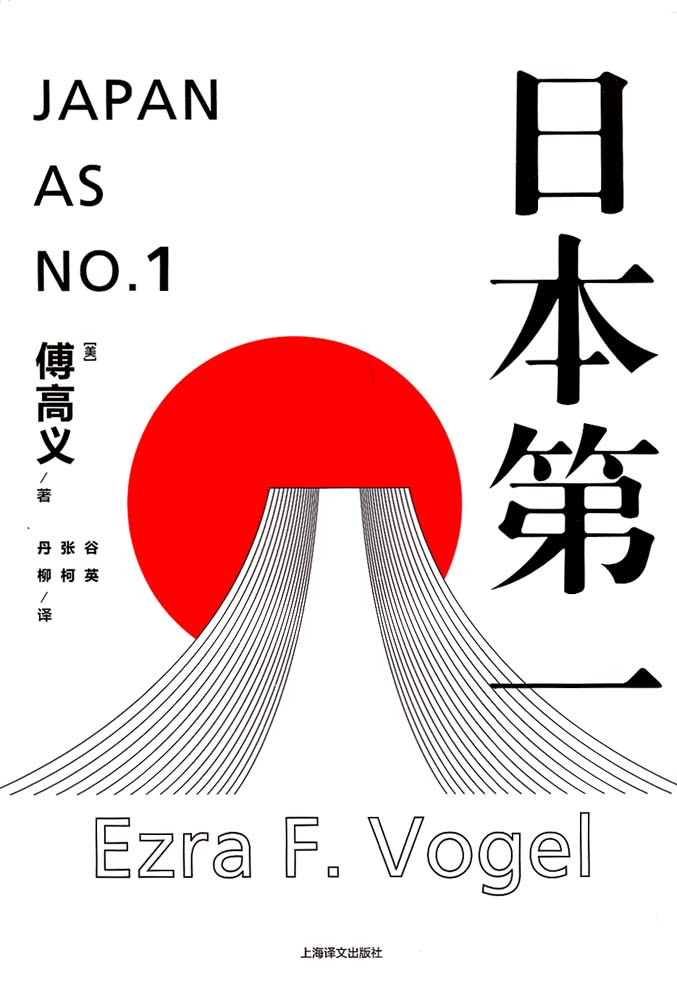 2009年,《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出版,让很多中国读者知道了傅高义这个名字。 2009年,《邓小平时代》一书的出版,让很多中国读者知道了傅高义这个名字。
而傅高义发表个人的第一部专著,则早在1963年。他以一部《日本新中产阶级》,开始了对日本的研究。1979年出版的探究日本崛起之道的作品《日本第一》,则为傅高义奠定了美国“日本通”的地位。
日前,在上海译文出版社举办的关于《日本第一》一书的主题读书会上,多位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畅谈了对此书的认识,以及此书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一本启示之书
王玉梅(上海社科院党委副书记):
1979年,日本社会经济高速发展之时,傅高义教授出版了《日本第一》这本书,研究总结战后日本复兴之路的特质,在全世界引起了很大反响。1980年,这本书首次被引入国内出版,30多年后重新出版,再次证明了这部作品对当下的意义。对中国读者来说,《日本第一》是一把认识日本经济社会情况的珍贵钥匙。
王泰平(《日本第一》译者):
日本与我国一衣带水。对国人而言,日本是一个既近又远的国家。今天,我们应该重新认识日本。同样,日本也要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的变化和进步。如果中日之间还是用老眼光看待彼此的话,可能会失去一些机会。
傅高义教授在为此书新版所写的序言中这样说明:“我说的‘日本第一’,并不是指日本经济是全世界最强大的,而是要告诉美国人,日本将如何发展。”他认为,30多年过去了,当年日本的那些优良特质今天依旧存在,而且有些方面比以前做得更好。
书中提到的当时日本存在的问题,如今有些也在我们国家上演。所以,我想我们不妨看一看日本是怎样走过来的,借鉴一些经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日本第一》可以看做是一本启示之书。
从研究学问出发
丁幸豪(上海美国学会名誉会长):
我想聊聊傅高义这个人。傅高义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原来是研究社会学的,后来转向了政治学,具体来说是地区研究。而他最感兴趣的是东亚地区。
傅高义做研究非常严谨,他的很多书和文章都是基于大量的调研写出来的。他写《日本新中产阶级》 时,就到日本去住了两年,一个一个地找人谈,了解真实情况。他很关注中国的情况,上世纪80年代他到广州住了七个月,写了一个名叫“改革中的中国——广东领先一步”的报告。可以说,他是一个国际学者。
我们再来聊聊《日本第一》这本书出版的背景,那时,由于日本的崛起,美国的反日情绪一点点高涨。我1984年在华盛顿,看到有一天《华盛顿邮报》刊登了一张照片,照片反映的是,一名议员参加议会时拿了一台日本产的电视机,说现在美国的老牌子都没有了,大家用的都是日本货,当场把电视机砸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傅高义出版这本书当然有很大的压力,但尽管有这样的压力,他还是把自己看到的、观察到的、研究的成果发表了。他是从研究学问出发的,实事求是地写。当然,他并不是说日本什么都好,还是有很多问题存在的,只是希望美国和日本能够互相学习借鉴。
傅高义现在退休了,但还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写东西。我认为像他这样的学者,他的学术精神、研究风格、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用学术的笔调写畅销书
任军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我觉得《日本第一》是和时代密切契合在一起的。
《日本第一》和《邓小平时代》的风格很接近,可以说都是用学术的笔调来写畅销书。写学术的畅销书,最关键的是要有前沿性,有好的选题。傅高义教授的选题敏感度极强。此外,畅销书还需要研究者的学术驾驭能力,包括文字的驾驭能力。傅高义教授的这种能力显示是很突出的。
我们学习他者,当然要研究他者、理解他者。只有理解了,才能发现他者的根本、他者优秀的品质,才能真正学会取舍,汲取他者的精华并抛弃自己不足的地方。所以,这本书所形成的这种学术模式,对中国学界也提供了一种新的启发。
哲学性的思考
樊勇明(复旦大学金砖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我先举个例子,前不久日本熊本县大地震,对日本的经济、社会管理乃至政府的效率都是一个考验。我关注到,地震后两分钟内,日本的电视台便开始播报地震的具体位置,五分钟后有了当地情况的报道,不到一小时,有了地震图像,救灾指挥部已经成立。到第二天中午,整个受灾地区的交通全部恢复。这些都很具体地反映出日本社会运转的效率。
可以说,现在我们对日本的研究还是不够的,我希望《日本第一》这本书的再版,能给当下学术界一个研究日本的新契机。
王少普(上海交通大学环太平洋研究中心主任):
从哲学上来讲,认识一个复杂的事物一般至少经过三个阶段,所谓的正反合。傅高义写的这本书,是在第一个阶段,以美国人为对象,展示日本在战后复兴中的一些哲学性的思考。
日本的发展战略相当注重依托一些传统优势,发挥好这些传统的优势,对传统文化进行很好的继承,这一点很值得我们借鉴。我们应该想想我们的传统优势是什么?以及怎样联系传统优势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