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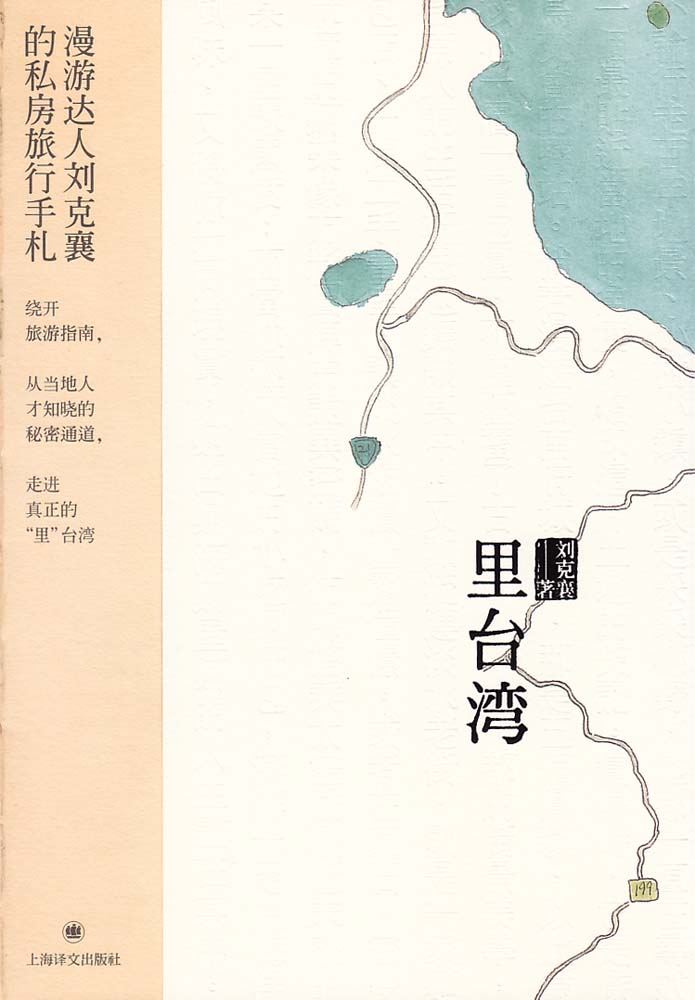 很多美好的生活,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样的故事,许久未听闻了。 很多美好的生活,来自同一个地方。这样的故事,许久未听闻了。
前几年,来自池上乡下的女生潘金秀迢迢北上,在台北公馆汀洲路,月租两万元,以一间小屋作为面包烘焙坊,专做吐司。她的食材加入大量来自家乡的谷物,结合邻近的初鹿鲜奶,手工费心制作。没多久即树立口碑,光做网络宅配即供不应求。
业务蒸蒸日上之际,她却因父母年纪老迈,毅然舍弃现有,返乡就近照顾双亲。日后改在自己的老家租屋做面包,仍旧不设店面,不要求量产。她相信质地好,透过网络团购,就算在偏远的小镇,一样能过自己想要追求的日子。
潘金秀每天早上出门,最喜爱穿过家乡的稻田。在路上,经常遇见一位近九十岁的老人。
老人彭立基,曾是日本军伕,远赴南洋打仗。战后回乡,拉过保险、卖杂货、当媒人等,后来就不曾离开。十多年前,他开始在海岸山脉种果树,因为整个镇都在朝无毒、有机稻米的方向发展。活到老学到老,他也不施化肥不喷洒农药,种了满山的脐橙和柳丁等。
刚开始当然不断失败,怎知这几年终于种出心得。除了果农抢着来收购,每天早上他都会摘一些到市场摆摊,纸牌上写着出产地和有机身份。还有价钱比一般人便宜,欢迎试吃。生意这样做一定亏本,但他觉得自己已逾米寿之龄,人生够了,应该多跟人分享快乐。
彭立基骑摩托车,载满蔬果出门,抵达十字路口时,大概也会和一位从事乡土教学的女士擦肩而过。
简淑莹老师熟稔小镇地方文史。四十年前,父亲在街上开了家书局。这是个以种稻为主的小镇,但他们家从台北引进了许多当代的书籍,店面仿佛小型图书馆。她从小在书店看顾,一边也阅读长大,见识比一般大学生成熟。
如今网络时代到来,台东的书店一家家结束营业。他们不愿意收手,继续卖书的服务。或许,也接受现实环境的改变吧,空出一角,提供咖啡饮料。但街上店面仍高挂着”池上书局“,几个书法大字浮凸,强调着人文的内涵。
他们三个人身上都有一个特质,初认识时,很喜欢搬出自己家乡的地名,或者把家乡的物产推销到台面。
”我是台东池上人“,”来自池上的某某某“。很少地方人士在自我介绍时,还会加上小地之名。”池上“这两个字,对他们好像是一个LV那样的品牌。
在那儿旅居时,我一直撞见这样的人物,不管离家许久,或不曾远行的,都有这样的骄傲。也不只是他们,好些人在自己的本分工作上,都抱持着某一生活信念。
二十多年前,不少小乡镇都有这种美好的自信。还记得来自美浓、东势或埔里的人,邂逅时,提到自己的家园,脸上也会浮现这么点滴的在地光荣。
曾几何时,这种在地自豪似乎少了,稀薄了。但为何池上还有,而且不减?究其因,因为那儿的稻米栽种不论有机或惯行,始终坚持品质。经过一番努力,台湾内外都打出名号。地方米价提高后,农民生活有稳健的保障,人人充满自信,对未来也展开各种梦想的追逐。
做吐司的女孩怀念在这样的家园长大,愿意回到家园从事烘焙业。旧书店的女儿纵使知道没什么利润,仍然坚持维持书店的门面。种柑橘的老人因为生活惬意,卖果物只为了快乐。这就是池上人,有梦想支持的小镇。
难道其他乡镇没有类似的期待吗?应该也有,只是经过几十年都会变迁,大家在外打拼,处于全球化、商业消费的冲击下,遮蔽了返乡的视野。重回家园的价值和意义,自然也消失了。
四年前一回旅居,结交了这些在地朋友后,遂常有联络。难得路过,一定去拜访,或者寄一两本自己允当的创作,请其指教。他们也常寄送地方物产,跟我分享时令收成。我藉着一物一产的悉心食用,怀念小镇的丰饶,他们则以物产的各方递送,继续告知小镇的美好韶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