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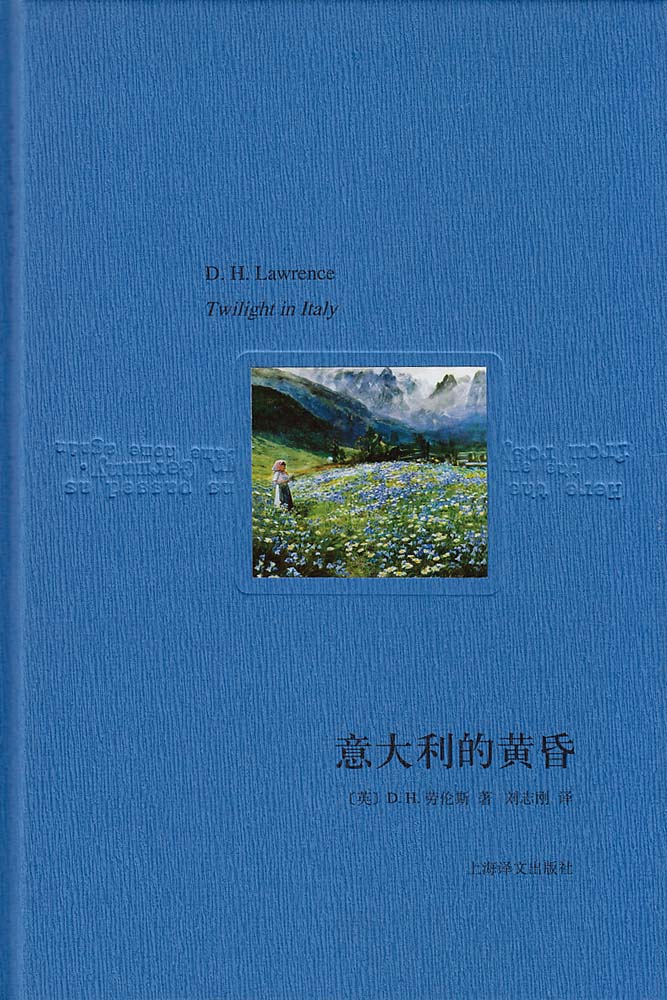 劳伦斯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和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四海为家的人生中,总共有三段旅居意大利的经验:一战爆发前在加尔达湖区(1912年—1913年),一战结束后在西西里岛(1919年—1922年),以及晚年养病在佛罗伦萨(1925年—1927年)。《意大利的黄昏》是劳伦斯的第一部域外游记,见证了他与意大利的初次相遇,也记录了作者在旅途和客居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思。 劳伦斯的一生虽然短暂,却和意大利结下了不解之缘。在他四海为家的人生中,总共有三段旅居意大利的经验:一战爆发前在加尔达湖区(1912年—1913年),一战结束后在西西里岛(1919年—1922年),以及晚年养病在佛罗伦萨(1925年—1927年)。《意大利的黄昏》是劳伦斯的第一部域外游记,见证了他与意大利的初次相遇,也记录了作者在旅途和客居期间的种种见闻与感思。
话说重头,劳伦斯与意大利的缘分还得回溯到1912年。那年4月的某天,他应邀参加了一场家庭餐会,而设宴的正是他原先在诺丁汉大学的法语教授威克利。那时候,劳伦斯仍未走出丧母之痛,而感情生活又颇多纠葛,加之肺病二度来袭,可以说,这是迄今为止他最潦倒、最失意的人生低潮。然而,就在那次餐会上,女主人的出现似乎让他的生活瞬间发生了逆转。弗里达·威克利,出生于德国的贵族家庭,20岁那年远嫁到英国,她与教授结婚12年,育有二女一男。相比之下,劳伦斯非但出身卑微,而且27岁的他还比弗里达年幼5岁。然而,就是这一眼之缘,立刻点燃了爱情的熊熊火焰。又过了三个星期,两人便开始策划私奔。5月3日的下午,这对叛逆的爱侣怀着忐忑又兴奋的心情,怀揣着仅有的11英镑,坐船渡过了英吉利海峡。弗里达打算直奔德国老家梅斯,将这重大决定告诉家人,顺便参加父亲军旅生涯50周年的庆典。5月7日,劳伦斯和弗里达在梅斯镇上闲逛,不料竟被当地军方扣押,罪名是私闯军事设施、意图窃取情报。不过,所幸弗里达的父亲德高望重,经他的求情,劳伦斯于次日即被释放。可是,既然已有英国间谍的嫌疑,劳伦斯决定还是暂且离开这是非之地。然而,热恋中的男女到底经不住相思的煎熬,于是,不久两人又在慕尼黑重聚了。为了节省费用,他们在城郊租下了一间小套房,共度了天堂般美好的一段蜜月。可是,这样的日子毕竟过得太清苦。他们省吃俭用,两个月花费还不到10英镑,可仍然入不敷出。于是,在弗里达姐姐的建议下,两人毅然决定移居到生活费用较低的意大利。
8月5日,他们踏上了漫无目的的旅程;他们只知道一直向南,因为据说阿尔卑斯山的南麓风景优美、气候宜人。劳伦斯和弗里达将三箱行李先行托运到奥地利南部的里瓦,而自己则打算徒步旅行。两人从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出发,一路上翻山越岭,遭遇了各种恶劣天气:饿了就拿出随身携带的小酒精炉,胡乱煮些吃的聊以果腹;困了就找间干草棚倒地而眠。好几次,弗里达实在受不了那委屈和折磨,两人也会坐一趟火车。然而,艰辛的旅途也一样给他们带来了惊喜。在荒废的古驿道上,在山顶积雪的映照下,沿路的十字架与基督像渐次映入了眼帘。在巴伐利亚,它们的模样陈旧、灰暗又抽象,基督则完全是德国农夫的模样。他虽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但躯体仍旧完美、贞定,成就了其永恒的存在。沿着伊萨尔河溯流而上,奥地利境内的十字架大多更为硕大、醒目,基督的面部和身体在在表现出极致的痛楚和完全的死。在这里,基督象征着死亡的幻灭与终结,而他的雕像也折射出人们对死神与痛苦手段的崇拜。再翻过阿尔卑斯山绝顶的关隘,进入南麓的蒂罗尔山区,这里的基督像更为多样:有的姿态优雅,在十字架上表现出自豪与满足;有的则纤弱而感伤;还有的毫不掩饰肢体的伤残,脸上甚至露出忿恨的表情。凡此种种,无不引发劳伦斯的思考:何谓存在?永恒的存在与人世究竟有何关联?夏日的某个午后,山里突然下起雷阵雨,劳伦斯目睹主人一家如何匆忙将铺晒的干草抱回草棚。冰冷的雨水浇淋在劲健、温热的身体上,干草的暖香则由怀中沁入到心脾。“这是十分愉悦的体验,是各种身体感受火热的交融。它让人心驰神醉,就像吞食了催眠的仙丹……”似乎就在这一刻,他感受和领悟到了存在的根基:艺术、宗教和劳动,人世的一切全都基于感性经验;生命是体温,是热血,是肉体的感知,理性与智识也无可替代。而这所谓的血性意识,除了驿道两旁的基督像,在山里还有它对应的自然象征–山巅的皑皑白雪以及它在天心投射的辉光和异彩。那是恒常不变的存在,人生与世间的一切经验无不向着它涌动、变幻。劳伦斯后来将这段旅程记录下来,一共写了七篇札记,其中“蒂罗尔的基督像”改名为“山间的十字架”后收入了本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