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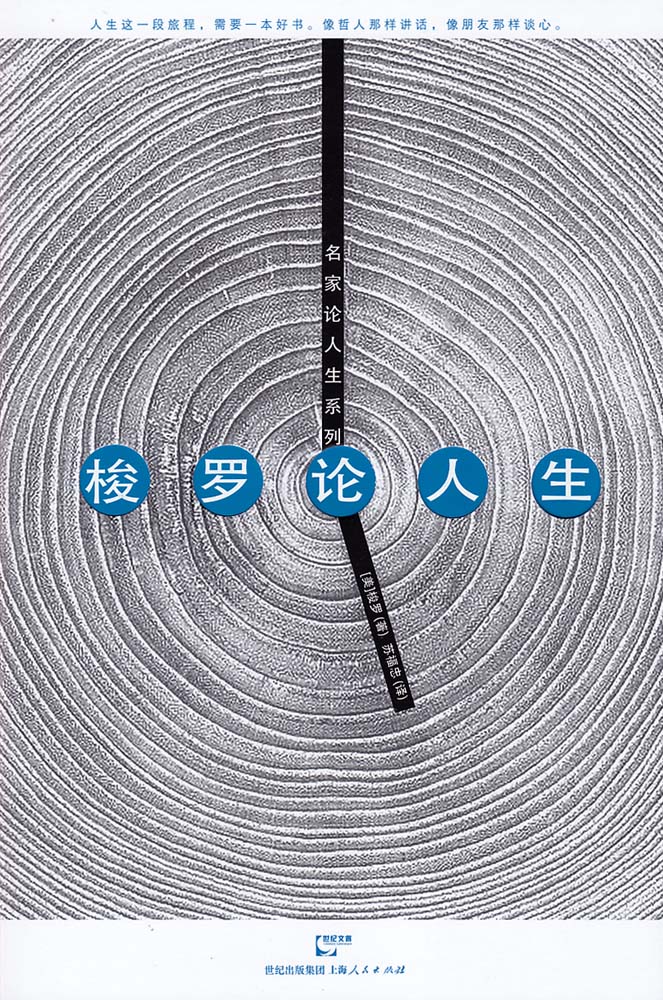 人生的另一种思考 人生的另一种思考
——译序
1
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美国随笔作家”的E.B.怀特,在纪念梭罗的《瓦尔登湖》发表一百周年之际,写下了一篇见解独到的散文《夜之细声》,其中有这样一句话:“实际上,赞美这本书有时倒让人难堪,因为大多数人都懵懂地认定,作者是那种未开化的人。”这话背后的意思,大概是指读书的一种起哄现象。都在说哪本书好,大家就跟风去读哪本书。至于为什么好、怎么好、好到什么程度,则很少有人再去深究。作为《瓦尔登湖》的译者,我倒是对怀特话中“懵懂”这个词儿更有感触。当初译完《瓦尔登湖》,我确有“懵懂”的感觉。不是《瓦尔登湖》里的什么章节不懂,也不是不明白全书在讲什么,而是对梭罗为什么写这样一本书有些“懵懂”。美国一些学者评说梭罗,认为他所以名留文坛,一是因为他在森林里修造了一所小木屋,远离尘嚣住了两年多;二是因为他写出了《瓦尔登湖》这本书。用这样的评论界定梭罗,我以为,和我一样,属于对梭罗懵懂的人。因此看来,即便是梭罗身后的同胞,甚至专家学者,对梭罗这个人以及他的所作所为,大多数人的理解还是很有局限性的。
“我独处时特别精神。如果我一周有一天有人陪伴,除非是我能叫出名字的一两个人,我发觉这个星期的价值对我来说大打折扣。它把我的日子搞乱了,往往要我再花一个星期才能调整过来。”这是梭罗写在日记里的话,而梭罗的日记是他二十岁以后开始写的,而且有些日记还做过修改,是很成熟很自觉的写作。他写日记一直写到他去世;他去世后经过整理出版,日记多达十四卷七千多页,算得上他一生的记录,主要记录他的思想轨迹。梭罗喜欢独处,这在他的文字里有多处流露。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后没有就业,回了家乡,做些零活,在朋友家住过,也帮助家里的铅笔厂干活儿,后来大部分时间里就在和大自然打交道了。从热闹的地方,一步步向僻静的去处隐去,很能说明梭罗喜欢独处的性格。也正是这样的人生轨迹,引发了世人的发问:一个大学毕业生,而且是一个美丽顶级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怎么非做一个不务正业的大闲人呢?躲开人类创造的那么多舒服条件,自己不觉得受罪吗?远离热闹的人世间,不觉得孤寂难耐吗?……不可否认,梭罗儿时随父母游览过瓦尔登湖后,产生了“瓦尔登湖”情结。但是,他成年后到瓦尔登湖畔修造一所小木屋,住了两年多,则是他决意以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人类只有简单的生活,才是真正的“天人合一”。用怀特的话说:“《瓦尔登湖》叙说了一个人如何给两股相反的强大动力撕扯——一股是享受世界的愿望(不因一只蚊子翅膀扇动就脱轨),一股是让世界恢复正常的冲动。”梭罗的“正常的冲动”就是他的自耕自足、钓鱼、采摘浆果、与动物和睦相处、与邻居和睦来往、探索森林、聆听声音、读书与思考。是的,思考对他来说很重要,是他一辈子最忙碌最擅长的事情,是他的更高级的人生阶段。然而,“让世界恢复正常的冲动”,凭梭罗的一己之力,无异于蚍蜉撼大树,遭到的是无情的打击。他居住在林间期间,这种打击说来就来了。他因为六年多拒绝缴纳人头税,在他去鞋匠的小铺修鞋时,被抓进了镇子的监狱,坐了一夜大牢。虽然他的好邻居替他缴纳了人头税,把他保释出来,但是他并不领情,经过认真而深入的思考,写出了不朽的《论公民的不服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