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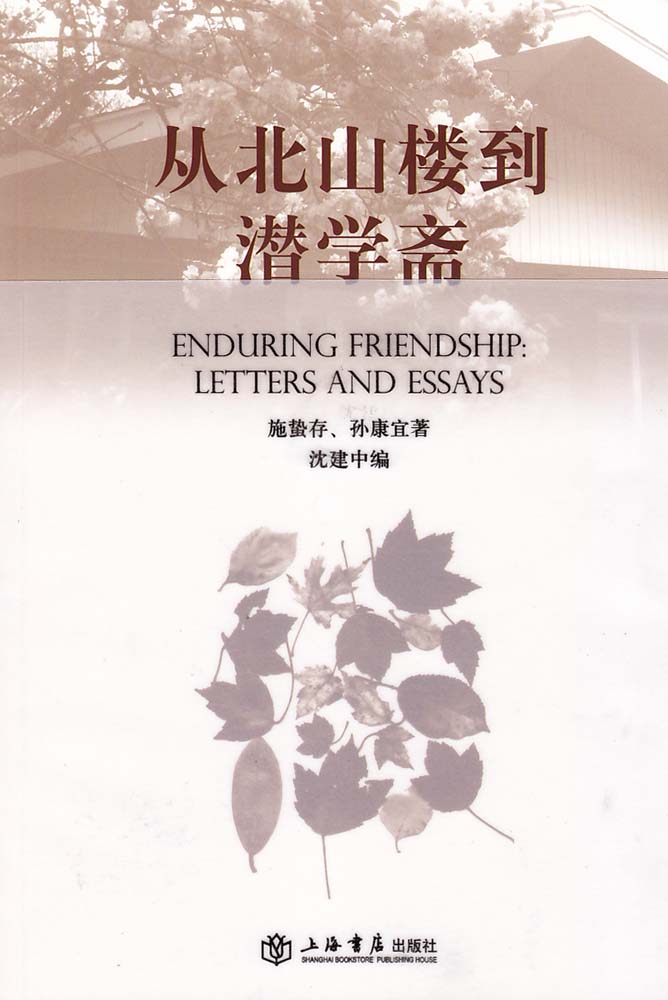 一 一
1990年代,我时常往北山楼请教,施蛰存先生曾法书几幅字贻我,其中有一幅“惟精惟一”,我当然遵照,心无旁骛,亦不二用。但印象里经常在我临走时会让带几封信下楼投入邮筒,至于他是给谁写信、写得啥,我一概不闻不问。2001年3月底施师母突然过世后,从此我不往打扰他老人家。2002年国庆节后施先生通知我去,送我一部《北山散文集》(二册),浏览了几天,翻到最后的施先生书信,绝大部分都是首次看到,我特别注意到其中致孙康宜教授的十八通信,真是大开眼界。两个月后,由于倦怠,一下子失去了施先生的十二册日记,我预备放弃正在编撰的施先生年谱,即“掼纱帽”——— 现在想来可笑可恶得很哩。
不觉到了2005年秋间,12月1日是施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想到北京闻广老人寄赐我的施先生致其父闻宥先生的两通信札,一是1938年施先生利用暑假回沪省亲,绕道香港时所作;信中详细陈述途径河内参观及访书情形;二是1940年施先生离开昆明前夕所作,讲述昆明物价形势,云南大学文法学院、文史学系的动态和其他学者情况。更要紧的是这两封信使长期悬而未决的施先生抗战时期辗转河内、香港和上海的时间地点,有了明确线索。我还想到沪上黄屏老师贻我两张施先生1938年的底片,一为在云南大学校舍留影;一为返沪探亲与夫人陈慧华在岐山村寓所合影。
这些材料到了我手头“如捏着一团火,常要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鲁迅语)。当时不见有何纪念活动的动静,况且既已不作“年谱”,何不请报纸发表,为有志的研究者作家们提供资料,藉此纪念施先生百年诞辰。经《文汇报·笔会》主持人周毅君首肯,《施蛰存书简两通》如期刊出,当日上午恰好我在开往苏州的列车上购得这份报纸,欣慰不已。
不久后,在陈文华教授敦促下,我恢复编撰“年谱”,并在她的指导下定名为《施蛰存先生编年事录》。文华教授为了支持我,甚至愿意为我设法寻回失去的资料。就在那时施先生的往来信件已大量散见于市肆,我突然发现往来书信更能弥补日记材料,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急中生智”,但我渐渐地确定了以书信为主体,辅以施先生叙事文录、相关报刊和其它史料等的编撰方法。
从此,我开始走上了一条竭尽全力地搜集采录施先生往来书信之路,一发而不可收拾。
二
通过几年的不懈追寻,我逐渐知道施先生所作书信的产量甚巨、涉及面广,他一生究竟写了多少信,实在难以估算,肯定是亡失更多。但以我曾经过录的施先生致河南崔耕先生函达三万六千余字、致上海范泉先生函有一万五千余字、致广州黄伟经先生函近七千字;再从主要收信方估算,以中原、蜀鲁为研究金石碑版区域,以闽粤为交流诗词杂文区域,以苏杭为收集藏书雅玩区域,以北方、苏皖为《词学》集刊作者读者区域,以晋陕为唐代文学研究赏析区域,这仅是我据大致印象的归纳,很不确切,然可借喻施先生所作书信的广泛性而已。再举辜健编《施蛰存海外书简》为例,收录致美国、香港、台湾和新加坡友人十八位,计二百九十七通,二十三万四千字数。——— 以上极大部分集中在1980、1990年代所作。
我推测,施先生早在中学时代向报刊投稿即写作书信。他又说,中学毕业后,浦江清就读南京东南大学,自己在杭州之江大学,“我们每星期都有书信往来”。目前我见到施先生较早的完整书信是刊于1923年11月20日《最小报》上的《致马鹃魂书》。他曾回忆主编《现代》时“给投稿人的信,少说也不下百余封”,听他说,每次从松江休假归来,光复信就得费时二三天,起码抽掉两罐白金龙香烟;现存的复投稿人宋清如函,就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千字文。如今在《现代》“编辑座谈”“社中日记”里均能见到他频繁与作者、读者的通信印痕。粗略可见施先生写作书信的轨迹,从1920年代《最小报》《世界小报》刊登其书信,到1930年代主编《现代》,再到1940年代主编《大晚报》副刊,直到1980年代起主编《词学》,施先生一直保持勤于写信的习惯,而产量之大,在他的同辈、同行中都是出类拔萃的。
因此,我认为施先生毕生都很喜欢写信,这是他与生俱来的风度,也成为他的日常生活方式;而并非仅仅是因为他交游广、活动多而造就的。
2005年秋间,我逐步收集了一批施先生往来书信,待到翌年下半期价格猛涨,当时网上有一通三页浦江清致施先生手札,标价万元,我打了几次电话还价,甚至恳求花费抄录,商贾坚不许;而此时沪上“秋拍”乍起,相关书信越见越多,只得“望洋兴叹”。此后我干脆侧重于在拍卖图录、网站报刊上搜寻采录,放大镜成了我的好伙伴。友人尹大为君给予我热情襄助,总是将藏品供给采用,诸位师友也纷纷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