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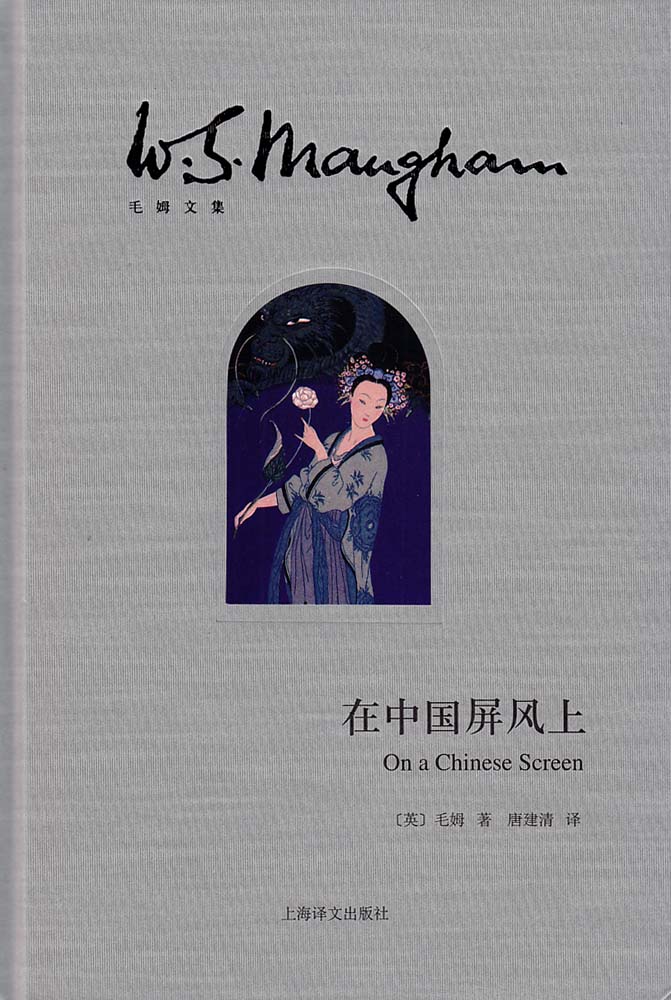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984—1965)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在其漫长的生涯中,读千卷书,行万里路。1920年,他东行抵达中国,《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是他的中国游记,五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游记的读者大抵是本国人,毛姆为英国同胞展现的是一幅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 毛姆(William Somerset Maugham,1984—1965)是著名的英国小说家,在其漫长的生涯中,读千卷书,行万里路。1920年,他东行抵达中国,《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 1922)是他的中国游记,五十篇长短不一的文章连缀成“一组中国之行的叙事”。游记的读者大抵是本国人,毛姆为英国同胞展现的是一幅古色古香、散发着浓郁东方情调的“中国屏风”。
毛姆在这架屏风上描绘了遥远、古老而又神秘的中国景致,她的山川风物、人文景观:令人敬畏的长城、急流险滩的长江、天光云影的水田、纪念先祖的牌坊、筑有雉堞的城墙、各式各样的庙宇、竹林深处的农家、山上的婴儿塔、路边的小客栈、随处可见的“苦力”,以及二十年代初中国的战乱、贫穷、肮脏,还有那位学贯中西、满腹经纶、哀叹道统衰落却又吸鸦片逛妓院、扎着一条细长的灰辫子的现代大儒形象!
毛姆的“中国屏风”无疑为英国读者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的中国形象,但对毛姆和他的英国读者来说,这一异国形象呈现的既是特定时代的中国现实,也是毛姆作为一个“观光者”个人及英国读者集体的想象物。在他们看来,或在他们想来,中国是一个既古老又神秘的国度。她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有着悠久的文明,但她的历史似乎是停滞的,现代中国更是落后、愚昧、贫穷,而中国人也让他们难于理解:一方面善良、热忱、孝敬父母、疼爱孩子,另一方面则圆滑、残忍、好说谎、不可信任,等等。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当然不是道听途说、甚至向壁虚构的产物,但走马观花确又难免雾中看花,正如他自己意识到的,“你所见似乎千篇一律,因为不管怎样,在异乡人眼里,每个中国城镇都大同小异”。所以在西方人看来,中国人不是买办就是苦力,而毛姆所见,中国的街道常是拥挤的,旅店常是肮脏的,苦力永远穿着破旧的蓝衣衫。
屏风具有呈现、点缀的功能,但同时它又是一种遮蔽。这架中国屏风“隔”在毛姆与现实中国之间,尽管毛姆有敏锐的观察力和真诚的同情心,但他对真实的中国还是有所隔膜的,因而,他描绘的中国形象又是一幅误读之图。在他笔下,中国的鸦片烟馆干净明亮,一派温馨怡人的气象,“这地方真令人愉快,像家里一样,舒适温馨,令我想起柏林那些小酒馆,每天晚上劳累了一天的人们常去享受安逸的时光。”面对陌生的经历,人们难免以熟知经验去加以理解,这真如毛姆所感叹的:“虚构总是比事实离奇”。当毛姆在一家旅店看到有个官员同苦力坐在一起喝茶聊天时,大为感动,觉得“这似乎就是真正的民主”。他进而推论:东方人的这种平等观念既不同于欧洲人,也有别于美洲人,在他们看来,职位和财富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地位的尊卑完全是偶然的,并不妨碍人的交往。这就显现出异国形象构建中的“乌托邦”气味来了。当毛姆由此提出:“为什么在专制的东方,人与人之间比自由民主的西方有更多的平等?”你会觉得这显然是个“伪问题”;而当毛姆自问自答:“臭水沟比议会制度更有利于民主”时,你自然哑然失笑,大可不必当真了。也许正是由于这种难于消解的“隔”,不通中文,只是到此一游的毛姆书中笔墨多半落在了在华的洋人身上,如传教士、外交官、汉学家、商人、海员等。个中情由他在《山城》一文中作了说明:
你说不出在你身边涌动着的这些众多的生命意味着什么。凭你对自己同胞的同情和了解,你有了一个支点;你可以进入他们的生命,至少是在想象的层面上,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真正地拥有他们。借助你的想象,你差不多可以将他们当作你自己的一部分。但这些人对你来说毕竟是陌生的,正如你对他们也是陌生的一样。你没有线索可以破解他们的神秘。他们与你即使有诸多的相像也帮不上你多大的忙,而毋宁更说明他们与你的不同。……你仍然像是看着一堵墙。你无所依凭,你不知道他们最基本的生活状况,于是你的想象就很受挫。
一种异国形象既是对“他者”的注视和观看,同时也是形象构想者的自我呈现,在此意义上,毛姆的屏风既是“中国”的,也是毛姆自己的。毛姆说他不是一个“勤勉的观光者”,确实,他本质上是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他对人生百态的好奇胜过异域风光。他“爱研究人性”。他观察细致、文笔生动,在不露声色的叙述中,人物的音容笑貌、才具性情跃然纸上,其中“亨德森”、“陌生人”、“大班”等篇,可以作为精彩的短篇小说来读。毛姆认为,“写作中,重要的不是丰富的材料,而是丰富的个性。”
毛姆的文字冷峻犀利,充溢着英国式的幽默,不经意间抉发出自负、可笑、贪婪、虚荣、做作等这些人性的通病来。毛姆的讽刺对象不限国别种族,那位中国的内阁部长虽然谈吐优雅,有很高的艺术品位,但我们读到这样一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