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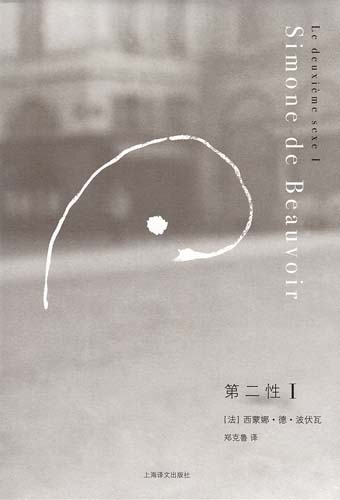 郑克鲁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现在还是成天待在学校里。因为他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里,平时看书、翻译甚至接待客人,都在这个书房里进行。他妻子也每天陪他待在这个书房里,毛巾、热水瓶、水果,什么都有,大有安居在书房的意思。 郑克鲁虽然已经退休,但是他现在还是成天待在学校里。因为他的书房(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就在学校里,平时看书、翻译甚至接待客人,都在这个书房里进行。他妻子也每天陪他待在这个书房里,毛巾、热水瓶、水果,什么都有,大有安居在书房的意思。
书房在上海师范大学文苑楼的最高层,安静、少灰尘、视野好,平时也少有人打扰,但前段时间他翻译的《第二性》获得了今年的傅雷翻译奖,来采访的记者陡然多了起来。老先生来者不拒,还担心自己说的东西又重复了:“他们问一样的问题,我就只能回答一样的答案了。不过来做书房的还是第一次。”
郑克鲁出生在澳门,曾祖父是著名大实业家郑观应。原以为他家世好,小时候应该读过很多书,想不到他说自己家里没什么藏书,父母对自己的读书更是毫不约束,“完全不管我的,爱读什么读什么”,以至于后来他能考上北大法语系,父母都觉得惊讶。
研究生毕业后正好赶上“文革”,被下放到河南信阳劳动,“前面几年时间法语荒废得厉害”。后来他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就找来两本书——法语版的《毛主席语录》和《法汉字典》,“都背了下来!”“文革”中仅有的这两本书,反而让他的法语有了更扎实的基础,“没有这段背字典的经历,后来翻译的工作还真是不行”。
80年代郑克鲁在武汉大学法语系担任系主任时,去法国做了两年交流学者。他现在的很多藏书,就是那时候一箱一箱从法国淘回来的旧书。“巴黎圣米歇尔大街上,到处是旧书店!”问他到底运了多少箱,他已经不记得了。他拿出一本80年代买回来的法语旧书,左拉的文学评论集,1926年出版的,整本书已经被他翻破,书脊上用透明胶带做了简单修补。“这本书是我比较珍惜的书之一。左拉的文学评论翻成中文的还很少,如果有空的话,我打算把它翻出来。”
现在他的书房地上堆满了书,大多是这几年托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上海的书店他偶尔也会去逛逛,但几乎没找到想要的书。“法语培训中心在中国有两家法语书店,北京和上海,但是上海的这家完全比不上北京的。上海的这家开在武夷路,青少年的书居多。”
郑克鲁是因1979年翻译巴尔扎克的《长寿药水》而走上翻译道路的,后来陆续翻雨果、大仲马等作家。他早年最喜欢的是巴尔扎克,到了晚年,慢慢地开始越来越喜欢普鲁斯特。而对于他不喜欢的作家,他就懒得翻译。有一次一家出版社想请他翻杜拉斯,被他拒绝了。“我觉得她的作品除了《情人》,其他都一般。”
B=《外滩画报》Z=郑克鲁
B:最近在看什么书?
Z:最近在看凡尔纳的《八十天环游地球》。我打算重译这本书,就开始看原版。之所以打算重译,是觉得现在市面上的译本都不大好。人们一般都觉得凡尔纳是通俗小说,语言比较简单,但是我现在看了之后才发现,凡尔纳的语言非常好,有时也很晦涩,不容易翻译的。
B:你现在怎么买书呢?
Z:我现在已经不大买书。实在缺什么书的话,就托朋友带。我有学生在法国,有时候我会托他给我带。有时候我还会让学校图书馆帮我订购,很多书都是图书馆帮我订购的。
B:你买书的标准是什么?
Z:我主要是看版本。倒不是一定要收什么珍稀的版本,而是要对翻译有用处的版本。比如我现在读的这本《八十天环游地球》,它正文后面的资料,包括对它的研究、考证就占了四分之一,我一般会收这样的版本。这对我的翻译很有用。
B:你现在做翻译,最常用到哪本辞典类的工具书?
Z:我用的是第二版的《小罗伯特法语词典》。这本词典真的非常好,每个词条的解释都很详细,还配有彩色插图。有很多人用《拉罗斯现代法语词典》,这本词典名气大,但是实用性来说完全比不上小罗伯特词典,很多词条的解释也没有它准确。
B:现在翻译家的稿费是不是比不上以前?
Z:那差得太多了!我现在翻《第二性》是千字60元,50年代时翻译一部《青年近卫军》就能买一座四合院,80年代一篇中篇小说的翻译稿费也能顶7个月工资!现在是最低了。我们这些搞翻译的,都只能全凭自己的兴趣和热情了。许多以翻译为生的年轻人,为了追求数量,也常常忽略质量,可能这也是现在翻译质量下降的原因吧!
B:你觉得小说、诗歌和戏剧的翻译方式存在哪些不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