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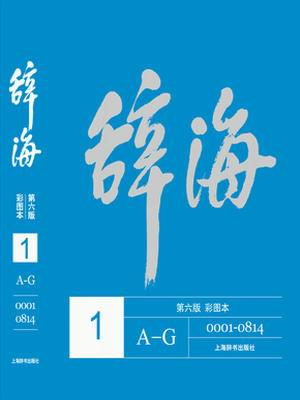 外派的究竟是“汉语教师”还是“中文教师”?“汉语教师”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而“中文教师”专教他们写中文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先生曾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他对汉语概念的辨析涉及《辞海》等多种书籍。 外派的究竟是“汉语教师”还是“中文教师”?“汉语教师”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而“中文教师”专教他们写中文吗?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郜元宝先生曾任澳大利亚悉尼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他对汉语概念的辨析涉及《辞海》等多种书籍。
1822年马礼逊编辑第一部英汉词典,其《英吉利国字语小引》谓“英文有二十六字母”,周振鹤教授认为这是“英文”一词最早的出处,1879年汪凤藻翻译《英文举隅》则用于正式书名。马礼逊译English language为“英吉利国话”,译Chinese language为“中国的话”、“汉话”,当时“英语”、“汉语”二词尚未发明。1855年何紫庭序《华英通语》:“吾友子卿……恒虑华言英语,不异北辙南辕”,才有“英语”一词;1862年唐廷枢出版《英语集全》,俨然已是正式术语(《“英语”与“英文”的首创权》)。
周君推测马礼逊造“英文”一词是从当时称满文为“清文”获得灵感,上世纪40年代周作人也说“汉文”乃与“满文”相对而生,“至于汉字则是新名词”(《十堂笔谈》)。其实“汉文”一词很早就有,南朝梁僧佑《出三藏记集》谈到佛经翻译时说,“或善胡义而不了汉旨,或明汉文而不晓胡意”,“汉”指“汉朝”。与汉唐佛经翻译相关的还有“汉言”、“秦语”、“秦言”、“晋言”、“唐言”,分别指汉朝、后秦、晋和唐朝的言语。北朝鲜卑族统治者称北方居民为“汉人”、“汉儿”,语言为“汉语”,始有民族和民族语言之义,但也不等于今天中华民族共同语的“汉语”(说见李一氓《试释汉族》)。至于1998年韩国发现的元代古本《老乞大》所谓“汉儿言语”,则是蒙元时的汉蒙混合语,明朝以后逐渐消失。现代意义上的“汉语”、“汉字”和“英语”“英文”一样都是“语言接触”的结果,并得力于晚清民族主义意识勃兴,周作人讲的不错,但他未指出“汉文”和“汉字”的发明者以及现代意义上“汉语”的由来。我见闻狭窄,不知有无这方面的系统考证。
汉语、中文、汉字(解放前一度定名为“国字”)、国语、国文、普通话、华语、华文等常用概念,源流异同,国内不讲究无甚大碍,但在“拿来”“送去”并行的今天,“送去”的对象难免疑惑,猝然问起,肩负“送去”使命的教师要给出满意解答,殆非易事。
目前高校“对外汉语专业”因“全球汉语热”而走红,“中国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简称“汉办”)声名远播,“送去”的是“汉语”,英文为Chinese 或Chinese Language,这都没问题。但Chinese或Chinese Language现在何以不叫“中国话”而叫“汉语”?落实到文字为何叫“中文”而非“汉文”?“中文系”全称为何叫“国文系”、“中国语言文学系”或“汉语言文学系”?外派的究竟是“汉语教师”还是“中文教师”?“汉语教师”只教外国人说中国话而“中文教师”专教他们写中文吗?“国语”和“国文”只是台湾地区的共同语和书面语吗?为何钱玄同、黎锦熙、罗常培等认为“国语运动”从清初刘继庄就开始了,胡适“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也不提当时的民国?China Town为何叫“唐人街”而不习惯叫“中国城”?明明是清朝衣服为何叫“唐装”?今日之“华”并非只是过去“华夏”、“华族”、“华夷”之“华”,“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共和国”也有一个“华”字,外人对中国的某些行为仍被称为“来华”、“访华”、“侵华”、“援华”,而“排华”、“反华”、“亲华”之“华”,既指本土中国,也包括海外华人。既如此,华语、华文是否只用来称呼海外华人的语言文字和文学?“海外(世界)华文文学”的主体不是既有过去的“华侨”也有后来的“新移民”吗?周有光先生说“‘国语’和‘普通话’这两个名词原来都是‘通名’,不是‘专名’——只有‘华语’这个名称有‘专指性’,一听就知道专指‘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可以跟‘英语’、‘法语’、‘日语’等名词并立使用。把中华民族的共同语定名为‘华语’,似乎比较合适”(《关于“大众普通话”问题》)他还预言“全世界华人可能在21世纪之末普及华夏共同语华语”(《21世纪的华语和华文》)这个说法的可接受性究竟怎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