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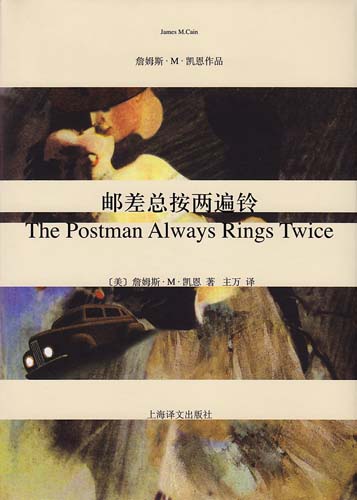 也许是出于某种微妙心理,成名小说家在谈及师承时往往大而化之,或是从莎士比亚到曹雪芹的陈年光谱上信手挑出一排名字,或是像某些本土作家宣称的那样:我从来不读别人的小说——便与“泯然众人”拉开了差距。印象中,对这个问题最为坦然的是村上春树,他对许多作家不遗余力的推崇,几乎成了国内出版社选题及营销的利器(村上君在腰封上出现的频率似乎不比梁文道少),由此而切实受益的至少可以数出雷蒙德·卡弗、保罗·奥斯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三位。不过,毫无疑问,被村上讴歌得最为热烈的偶像当属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也许是出于某种微妙心理,成名小说家在谈及师承时往往大而化之,或是从莎士比亚到曹雪芹的陈年光谱上信手挑出一排名字,或是像某些本土作家宣称的那样:我从来不读别人的小说——便与“泯然众人”拉开了差距。印象中,对这个问题最为坦然的是村上春树,他对许多作家不遗余力的推崇,几乎成了国内出版社选题及营销的利器(村上君在腰封上出现的频率似乎不比梁文道少),由此而切实受益的至少可以数出雷蒙德·卡弗、保罗·奥斯特和雷蒙德·钱德勒三位。不过,毫无疑问,被村上讴歌得最为热烈的偶像当属司各特·菲茨杰拉德。
我一直怀疑,假如不是村上毕生都将菲氏奉为写作导师,假如村上没有假借《挪威的森林》主人公之口将《了不起的盖茨比》作为鉴定“自己人”的暗号,这部当代美国名著在中国的普及率是否会比现在更低,是否会有更多的人把这个忧伤的故事当成微软的发家史(曾在一家报纸上亲眼看到记者把书名写成“了不起的比尔·盖茨”)。
实际上,许多沿着村上的轨迹抵达菲茨杰拉德的人,看不出两者之间有特别醒目的连线。菲茨杰拉德对村上春树的渗透是全方位、弥漫性的,不是一幕场景、一个人物那么简单——爵士时代的纽约酒精稀释在六七十年代东京的空气中,局部的浓度反而不是那么强烈,那么好认的。要读到深处,方才能体会盖茨比式的言不及义,那种仿佛从一个梦境飘向另一个梦境的神态,常常从村上笔下顺势流淌出来,那样隐蔽,也那样自然。更不可思议的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虽然她曾著长文描述儿时在阁楼上读达希尔·哈密特(美国硬汉侦探派代表作家)读到昏天黑地,但我确实很难从她的《盲刺客》里分辨出《马耳他黑鹰》的气味。
相比之下,那本奠定了加缪江湖地位的《局外人》,作者就相当实在地指出了它的灵感直接来自于美国人詹姆斯·凯恩的《邮差总按两遍铃》。确实够直接。无论是篇幅、节奏感,还是情节的走向,人物基调的设定,《局外人》与《邮差》的血缘关系,都是我迄今所见最相得益彰的。相得益彰的意思,可以参见《无间道》的港版与美版——即便明明是一个模子里翻出来的,也各自具有对方无法替代的价值。加缪把解构的心机,更多地倾注在束缚人物的体制身上,这让作品具有更强的现实指向性;而凯恩的原著,则以更绝望的方式看待宿命,好像在冷冷地告诉你:没什么好挣脱的,认了吧。《邮差》的故事,浮在表面的是一宗美国潘金莲伙同西门庆偷情杀夫、现世现报的勾当,但实质上却是讲述一个人无论怎么躲,都被一只看不见的手推向绞刑架的故事。故事里充满了“二”,每到一个关键节点,主人公总是不能在第一时间听见命运的召唤,但它第二次就一定会铿锵在耳边。这种要命的荒诞感正是加缪一直想着力展示的,但直到《邮差》的问世,他才省悟,无须作者灌输,观念可以透过故事结构上的花样,用最沉默的方式达到最有力的效果。当《局外人》里的默尔索随朋友报复未果,明明已经偃旗息鼓,却又鬼使神差地揣着枪向门外走去时,我知道,凯恩的灵光,就像小说里那轮无处不在的太阳,直射到了加缪的笔下——正是这股能量在推动着人物,向着命运结结实实地撞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