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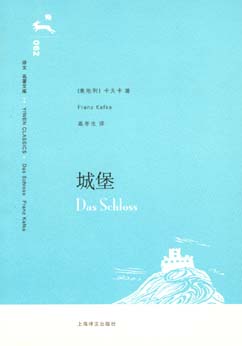 1924年6月3日,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逝世,年仅41岁。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生前鲜为人知,其作品也未受到重视,身后却文名鹊起,蜚声世界文坛。他的作品形式及内容均不受流行文学的影响,力图庇达当时一般的生存体验,人类的疏离、孤独、残破的观念,以及对暴虐之国家机器的恐惧心理。后世人们从中读出了20世纪社会生活普遍的焦虑与恐慌。 1924年6月3日,20世纪最著名的作家之一弗朗兹·卡夫卡(Franz Kafka)逝世,年仅41岁。卡夫卡,奥地利小说家,生前鲜为人知,其作品也未受到重视,身后却文名鹊起,蜚声世界文坛。他的作品形式及内容均不受流行文学的影响,力图庇达当时一般的生存体验,人类的疏离、孤独、残破的观念,以及对暴虐之国家机器的恐惧心理。后世人们从中读出了20世纪社会生活普遍的焦虑与恐慌。
他被称为“作家中之作家”。《城堡》是其最具特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
身份规定我们存在的方式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以各种各样的社会身份存在的。这些身份规定了我们存在的具体方式,也是我们存在的确证。当我们难以确定我们的社会身份,或者别人不承认我们的这种社会身份的时候,我们便感到失落与焦虑,感到失去了赖以确证自己存在的依据,存在于是会变成一场充满恐惧与不安的噩梦。卡夫卡的《城堡》便可以理解为人失去自己存在依据的可怕的噩梦。
土地测量员K在一个冬夜到达了一个村子,他接到通知,要前往村子附近的那座城堡去执行公务。然而,当他到达这个村子时,他发现自己无法证明自己身份的真实性与合法性。K去见村长,村长告诉他,他们没有测量土地的需要,更没有雇用他。村长确实也曾收到一个招聘土地测量员的公文,但那是几年前的事情了,而且他现在已经无法找到那张多少可以证明K到来的合法的纸片儿。K想进入城堡,想见到城堡的统治者伯爵,因为这是证明自己身份并开展工作的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他想得到一张进入城堡的通行证,为此他设法巴结结交各种各样的人:大臣、大臣的秘书、秘书的情妇、信使、信使的女儿……然而一切都是那么捉摸不定:大人物克拉姆始终只有一个影子;信使的身份则今人怀疑,到最后,甚至城堡的存在都成了问题,K为证明自己身份的所有努力都是徒劳,他只能以学校看门人的暂时身份在村子里居住,就连这种身份也随时面临威胁……
“我是谁?”“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这是一个人类追问了几千年的问题。哲学家就这个问题有各种各样的说法,但是这些说法不可能代替我们一劳永逸地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它与每一个偶在的个体具体的生存体验密切相关。在外在世界变化急促,传统的价值观念不断受到冲击的当代社会,周围的人与事常常让人感到疏远而陌生,人们对自我的确认于是经常遇到危机。
卡夫卡在他的《城堡》中表达的正是当代人的这么一种生存状况。他是以土地测量员的身份来到来到这个村子的,这一身份标明着他的使命,也标明着他存在的意义,是他在这里合法性存在的唯一的依据。然而,没有人可以为他的这一身份作证。而且,我们发现,不仅K无法确证他的身份,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的身份都难以确定。置身这样一个世界,怎能不让人感到不安与恐怖?
法国存在主义作家加谬在他著名的哲学随笔《西绪弗斯的神话》中曾说:“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在这个骤然被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里,人感到自己是一个局外人……这种人与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的分离正是荒诞感。”对生存的荒诞感的深刻表达,使卡夫卡和存在主义联系在了一起。而且,比起萨特、加谬这些存在主义大师,他提前了整整一个时代。
深刻的怀疑论者
在西方思想史上,卡夫卡是一个典型的怀疑论者。
在小说《城堡》中,卡夫卡通过主人公K梦魇一般的经历,形象地表达了自己深刻的怀疑论思想。城堡在小说中是一个人人都看得见, 人人都在谈论,而且人人都受着它支配的地方。然而,那也是一个没有人真正进入过的神秘去处。在进入村子的第二天,K为了证明自己,决定进入城堡。可是,明明城堡就在前面,却无法接近它,奔波了一天的K最后又回到了原来出发的那家客栈。由于一贯使用象征主义的表达方式,人们确信卡夫卡在这里表达的实际上是对人类生存的目标与希望的怀疑。目标历来在那里矗立着,然而人类任何追寻目标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在这个过程中,行动与不行动没有质的差别:《城堡》中向着城堡前行的K最终发现自己又站在了出发点上,小说《诉讼》中在“法”的门前等待一生的那个乡下人同样没有接近目标一步。一旦卷入,追寻目标的过程将是一个永无休止的过程,不但无休止,而且徒劳。“我知道,某处有这么一个地方,甚至能看到它,但是我不知道,究竟在哪里,也无法接近它。”“目标只有一个,道路却无一条,我们所谓路者,乃彷徨也。”在卡夫卡的札记里,我们发现了这样更直接的表达。这种孤独而又痛苦的人生体验,卡夫卡不断地述说着。它像一条毒蛇,纠缠着这位脆弱而又敏感的天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