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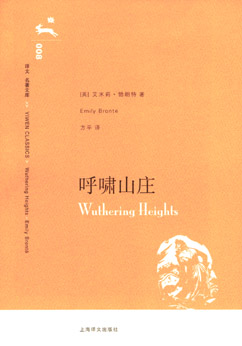 并非是病态 并非是病态
苏珊·桑塔格(Susan Santage,1933-2004)说:“任何形式对社会规范的背离都可以看做是一种病态。”
以英国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的世俗眼光来看,艾米莉·勃朗特和她的《呼啸山庄》(Wuthering Heights,1847)不啻为一种病态。尤其当他们发现,在作者埃利斯·贝尔的假面之下竟是一张柔弱而坚韧的女性脸孔。——勃朗特三姐妹最初是以贝尔三兄弟的假面登上文坛的。
那个时代,社会对于女性写作,就如艾米莉的姐姐夏洛蒂·勃朗特所说的:“人们对待女作家,往往怀着偏见。评论家有时拿性别当做惩罚的武器,有时又以此作为吹捧的因由。”
她们的作品得到的赞美并不能抵消所受到的攻击,尤其是艾米莉的《呼啸山庄》。野蛮、邪恶、粗俗、令人厌恶——评论家毫不留情地用最恶毒的语言鞭打这一部“病态”的作品。夏洛蒂·勃朗特在为此书再版作序时也不无歉意地写道:“假使她活着,她的思想自会像一株壮实的树木一样成长起来,长得更高更挺拔,更加枝繁叶茂,结出成熟了的更香甜、更红润的果实”。
作为女性,艾米莉·勃朗特的性格和作品却满溢男性的暴烈,就像她所迷恋的约克郡的荒原:暴戾、任性。她虽三次离家求学和谋生,却都因为思念家乡和那一片呼啸的荒原而回归,并且以后再也没有离开过。可以说,《呼啸山庄》这个色彩过于强烈的爱情故事是她对自己荒原性格的一种回归。她朴实尖刻的文字和哥特式的小说情节和氛围,她讲述的仿佛来自天国的、关于灵魂相吸引的痛苦和喜悦,就像是荒原那一阵阵的疾风,呼啸着掠过那个感伤、细腻、优雅的维多利亚时代。
艾米莉及其写作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她的性别。十九世纪的英国,写作的女性并不少,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和夏洛蒂·勃朗特是其中的著名代表。艾米莉既不像简·奥斯丁淑女般本分地、在男性秩序所容许的有限空间中自说自话;也不像姐姐夏洛蒂般叛逆、反抗又寻求皈依,反抗男性,又以另一种姿态依附男性。写诗的她尽管只留下这一部小说《呼啸山庄》,但这惟一之作中的死亡意识、自由精神、普世之爱、人性复归等,都超越了性别的牵绊和社会成规的拘囿,进入了对人性的沉思。
挣扎的灵魂
《呼啸山庄》是一个复仇的故事,里面交织着复杂且强烈的爱与憎恨。
复仇却并没有使希斯克利夫获得心灵的安慰。因为他的终极目标不是复仇,而是爱的复现,灵魂的皈依。这在小说一开始有所暗示。
他的仇恨报复在别人身上,也报复在自己身上。每一次猛烈的报复只会加深他内心的创伤。他在此岸疯狂破坏,祈求复归,而他爱之所在、魂之所依的凯瑟琳却在无法到达的彼岸。世俗的行为无法抵达那个彼岸,这种可怕的隔阂只有死亡能消解。当他意识到这一点,他便开始了通向彼岸之旅。一连串临死前的告白,概括了他在俗世寻找灵魂至爱的艰难旅程——那真是一场太长的搏斗。
关于爱,凯瑟琳寻求的却不是尘世的依靠,而是灵魂的对照:
“而我爱他可不是因为他长得俊俏,纳莉,而是他比我更是我自个儿。不管咱们的灵魂是用什么料子做成的,他和我是同一个料子。”显然,艾米莉的这个凯瑟琳不是简·奥斯丁笔下的中规中矩的淑女,在男权社会里展现有限的个性,寻找一个好的世俗归宿。她不是在寻找依附的大树,而是一个可以让她看到真实自我的同类。
一次偶然的事故,凯瑟琳见识了山丘之下画眉田庄优雅的贵族生活。那是一个与呼啸山庄截然不同的世界。
尽管凯瑟琳爱着希斯克利夫,但她也向往文明优雅的生活,以及上流的社会地位。她嫁给埃德加,只是嫁给一种文明的生活方式,获得一个尊贵的身份符号。从呼啸山庄到画眉田庄,凯瑟琳完成了一次致命的分裂。她既要世俗的荣华,也要精神的满足;她的冠着尊贵名号的躯体留在了田庄,陪伴着丈夫埃德加,而她的叛逆灵魂,却游荡在狂风暴戾的荒野,等待着另一个同样的灵魂的归来。
大病初愈的她经历了与希斯克利夫的一段暴烈的灵魂告白后又一次陷入疯狂。这种致命的灵魂碰撞对于凯瑟琳而言不是毁灭,而是至福,是永恒自我的回归。
“我在这世上最大的苦恼,就是希斯克利夫的苦恼;他的每一个苦恼,从刚开头,我就觉察到了。我生命中最大的思念就是他。即使其他一切都毁灭了,独有他留下来,我依然还是我。假使其他一切都留下来,独有他给毁灭了,那整个宇宙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陌生人,我再不像是他的一部分了……我对希斯克利夫的爱,好比是脚下的永恒的岩石,从那里流出很少的、看得见的源泉,可是却必不可少。纳莉,我就是希斯克利夫!他时时刻刻在我心头——并不是作为一种欢乐,就像我不能老是我自个儿的欢乐一般,而是因为他就是我自身的存在。所以不用再提我们两个会分开吧。这是办不到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