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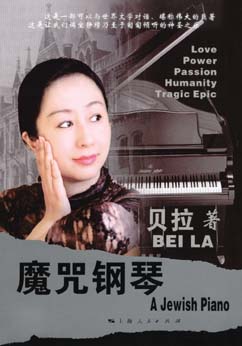 我们常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我们常说上帝与我们同在。
而事实上,当一个国家、民族、或者个人面临灾难、疾病、战争和痛苦的时候,上帝经常缺席,或者说不在场,迫使我们人类要独自承担所有的痛苦和不公平。那时候,我们能够做什么?做什么才使人类有尊严地活下去,并且创造出属于人的那份美好?本书通过一个悲情故事、一部种族和谐与文化包容的爱情交响,给了我们一个答案:我们只有学会宽容和爱,才能度过动荡不安的年代。
故事发端于二次世界大战。才华横溢的波兰钢琴家亚当是个忧郁的犹太青年,假如不是因为纳粹的排犹,他不会在1938年逃亡到列宁格勒;假如有一个和平的家,留苏的红军遗孤李梅就不会在苏德战争的前夕,与亚当相遇。他们像两朵漂泊在异乡的云,没有任何的征兆,便在音乐的殿堂里悄悄地相爱了。他们共同创作了四手联奏《降D大调第8号浪漫曲》,一个怀念祖国田园承袭舒曼和肖邦的激情,一个柔情万种骨子里燃烧的是中国古典。他们渴望爱情像两只自由的鸟、相拥的两朵云、连枝的两棵树、并挽的两株草。然而德军发动了“巴巴罗萨”的战争计划,大批的流亡犹太人再一次面临寻找家园的选择,几乎全世界的国家都向犹太人关上了大门。这时,一个关于中国的上海是犹太人的“诺亚方舟”的传说,使亚当和李梅同时被卷进逃亡远东的洪流。到达上海后,亚当和大批的犹太人先进难民营,后被圈入日本占领军类似集中营的虹口区犹太人“隔离区”。李梅因为是红军的遗孤,迅速进入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战争使他们的爱情只能在一次次的生死离别的眺望中,向上帝祷告。尴尬的是,李梅在新四军的根据地生下了一个金发婴儿,于是,在不幸中孕育出万幸的涟漪。种族、文化、宗教和爱情的冲突,在占领区的上海和解放区的苏北同时展开。
那是一个匪夷所思的苦难时代,生发出现代人难于想象的悲惨生活。
面临战争、屠杀、饥饿和病痛,笃信上帝、与上帝有十戒之约的犹太人,小部分人加入了抗战的行列,大部分人都陷入了等待上帝的无限茫然之中。倒是同样在苦难中挣扎的中国人,敞开胸怀接纳了他们。在善良的中国人看来,这些蓝眼睛黄头发的犹太人,比他们高级,是洋人。比他们高级且是洋人的犹太人受苦受难,犹如落难的王子公主,尤其令人同情。况且,在中国人的文化中,从来就没有种族歧视的遗传因子。于是,绝望中的犹太人得到了上海市民冒险援助,通过各种方式为他们偷运食品和药品,许多犹太人因此而保存了生命。李梅是这项冒险援助计划的策划人和实施者,亚当和他的族群教民心存感激。在1945年7月盟军轰炸日军仓库和电台时,误炸了虹口的犹太人的隔离区和中国难民区,大火烧掉了隔离犹太人和上海难民的围墙。于是,两个种族的人们终于融和。在十里长街的火焰和废墟中,抢救和被抢救,上演了一曲感动几代人的世纪悲歌。
抗日战争结束,内战又开始。亚当和李梅又错过了约会的时间和地点。新中国建立后,又因政治的原因,亚当和李梅总是咫尺难见。只有他们钟爱的音乐传达着无尽的思念和守望。他们相约在天堂里相见,把失去的岁月和爱一点一滴地捡拾回来。
看上去,这是一部浪漫悲情的史诗,但贯穿其中的却是神圣的信仰和人性的光辉。尤其是本书的下半部,“亚当”二世寻找精神家园在远洋罹难,犹太医生马丁像雕像一样守候在李梅的身边,他们用爱和宽恕甚至是同情和怜悯,共同化解着人世间的仇恨,以犹太人的视角为我们展开一幅另类的历史画卷:当一个国家轰轰烈烈地想“革”自己本民族“文化”传统“命”的时候,灾难已经不远了!
战争的苦难、诗性的思想、神圣的信仰、悲剧的力量、虚无决绝的浪漫情怀和艺术穿透力,所有这些艺术元素都嵌进在本书的故事和细节中,在人类共通的精神层面上与不同文化的读者沟通,它让崛起的中国向世界发出了这样一个信息: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抑或将来,汉文化熏陶下的华夏子民,是热爱和平的人道民族,有足够的胸怀和气度,融合不同的文化和文明。面对今日世界之文明冲突和宗教矛盾,曾经发生在二战时期中国上海的宽容和爱,跨民族、跨文化的睦邻和谐,为什么不能够成为当今世界和平之典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