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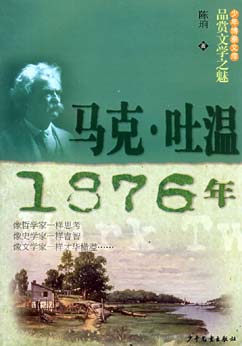 1876年,我们的主人公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克菜门斯)41岁了。这个晚熟的天才一贯对自己的事保持着可爱的天真和后知后觉,所以他并不自知正踏在人生起承转合的一年上。更何况1876年,这位漂泊了半生的作家正处在让人安心的家庭生活中。远离了哈特福德的社交圈,与妻子和两个淘气的女儿一块儿在夸克农庄的悠闲日子简直堪比仙境。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舒适,几近完美的小环境使马克·吐温的创作欲异常旺盛。于是,1876年的夏天,他天天躲在农庄里那间七面有窗的八边形小屋里,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沉思默想,安静的空气中只有笔尖“沙沙”划过纸端的声音。偶尔当思考告一段落时,马克·吐温就会抬眼望向远处的山谷和希芒河。渐渐地,美国文学史上最无拘无束的男孩——哈克贝利·费已经在他脑海里酝酿成形了。 1876年,我们的主人公马克·吐温(原名塞缪尔·克菜门斯)41岁了。这个晚熟的天才一贯对自己的事保持着可爱的天真和后知后觉,所以他并不自知正踏在人生起承转合的一年上。更何况1876年,这位漂泊了半生的作家正处在让人安心的家庭生活中。远离了哈特福德的社交圈,与妻子和两个淘气的女儿一块儿在夸克农庄的悠闲日子简直堪比仙境。一切都是那么平静舒适,几近完美的小环境使马克·吐温的创作欲异常旺盛。于是,1876年的夏天,他天天躲在农庄里那间七面有窗的八边形小屋里,时而奋笔疾书,时而沉思默想,安静的空气中只有笔尖“沙沙”划过纸端的声音。偶尔当思考告一段落时,马克·吐温就会抬眼望向远处的山谷和希芒河。渐渐地,美国文学史上最无拘无束的男孩——哈克贝利·费已经在他脑海里酝酿成形了。
大约在一年前同样这个季节,这个地方,汤姆·索亚——哈克贝利·费恩的好兄弟,已经跃然纸上。但直到1876年的夏天,《汤姆·索亚历险记》才刚刚上了美国勃里斯出版社的出版计划表,等着外界的评判。这是马克·吐温第一部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作家有点替它担心。这部沉浸在童年回忆中完成的少年儿童读物。虽然为自己与家人所爱,却不一定能让当时那些讲究规矩的东部人士接受。这位被称为乐观的“太平洋畔最狂野的幽默作家”,心里抱着“与其让人诟病,不如束之高阁”的想法,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怀疑自己的书是否值得出版。要不是当时作家的朋友,《大西洋月刊》主编赫威尔士阅读后力荐,劝他不要放弃,那个天真可爱的汤姆·索亚恐怕便难与世人相见了。
不过无论怎么担心,出版计划无从改变。所以1876年的马克·吐温考虑更多的恐怕还是在哈克贝利·费恩这个男孩身上。早在创作完《汤姆·索亚历险记》后,他就意识到生活在理想国中的汤姆必将被更成熟的哈克贝利替代。因为在转折的一年之后,难以一直躲在农庄,远离纷繁世事的马克·吐温自己也正发生着变化。
1876年,作家身处的年轻国家正在“黄金时代”的宣言里高速前进,白天人们拼命地工作,夜晚城市的狂热带来旺盛的消费。灯红酒绿,辉煌而艳俗。美国仿佛要把十一年前那场内战带来的压抑完全爆裂释放。过去被现在和未来挤压,踪影难寻。离开了年龄、思想、教育、心理、喜好、使命、灵魂、创造和发现,钞票被赋予了极度的张力。在这几乎是唯一的尺子下,属于人之心理的调剂天性被遮盖了。压力拼搏置换了人际的平和互补,功利身份改变了个人内心的思索,喧嚣浮华代替了人朴素而深沉的境界,金钱涌动的名义下,前者都是压过后者的合理而主流的表率。于是无数个人被甩入这个集群的“潮流”中苦苦挣扎。斯巴达克式的年轻和体力因而变得十分重要,备受推崇。巨大的经济发展,财富增长正以这个国家精神的枯萎、个人精神的疲惫为代价。在那个时代,连纽约街头的乞丐都会跟着腰缠万贯的大老板们重复这个国家正在蔓延的声音:祝您发财!祝您发财!
在这样的世事中长途跋涉了半辈子的马克·吐温在《汤姆·索亚历险记》里找到了一丝逃避和宽慰。但到了1876年时,这个避风港就显得不太现实了,盛夏的某日他终于动手写下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第一笔。这次作家塑造了一个在无法挣脱的现实中见弃社会、追寻自由的男孩形象。他比汤姆·索亚更现实,也更矛盾,因而更贴近1876年后马克·吐温重回密西西比河。探访故乡后的忧郁心境。
现在,130多年过去了,当这部历经八年创作的作品与1876年年底才出版的《汤姆·索亚历险记》一块儿摆在现代读者面前时,我们依旧承认这是晚熟的作家不世出的两部杰作。忽略了不同的主人公,两部书完全构成了一个男孩有些无奈的成长史,混杂着喜剧和悲剧,梦想与现实,荒唐的冒险与悲苦的人生。这个男孩就是马克·吐温自己,也可能是我们阅读者中的每个人。在写《汤姆·索亚历险记》时,马克·吐温仍然算是个小说写作的新手,但他却找到了非常适合他的素材,并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孩子的理想国,一曲成人美满的圣歌。因此在1876年出版后,虽然它曾被作家定义为儿童读物,却也受到了大多数成年人的热烈欢迎。到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家则创作了一部远比他自己想象中更伟大的作品。它现实地牵涉到了美国人,美国和这个国家独特的神秘性。难怪作为英国评论家的W·H·奥登要说:
“在浩瀚书林中,《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是了解美国的一把钥匙。正因为我们可以举出别的书——譬如《奥利佛尔·特威斯特》是反映英国人的态度的书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