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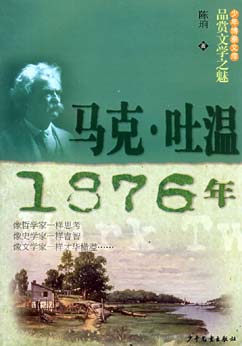 一段传奇的人生结束了。 一段传奇的人生结束了。
这个异常丰富的美国人,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多彩多姿的生活经历。他被尊崇为“最幽默的作家”,那在美国恐怕是最高的荣誉。
他似乎总想着同时做许多不同的事情。他疯狂地读书,同时又疯狂地旅行。他逃避南北战争,躲开格兰特将军,不肯当兵作战,但是后来又为格兰特作传。他乘蒸汽船,远渡夏威夷,在那个美丽的群岛创作了两本书,渐渐建立起作为作家的地位。但他的文学事业,却在旧金山、纽约蓬勃发展。虽然他酷爱写作,而且也有那份天才,但他却不能摆脱对钱的在意,也许是童年艰难求生的烙印,也许是难以脱离的国内大环境,他一有机会就要去做生意。虽然文人从商常常失败,但他从不甘心,拿到稿费就改行……
这就是马克·吐温——一个有魅力的人,但有时不是一个和善的人;一个很幽默的人,但有时显得刻薄;一个热爱自己国家的人,写的都是地地道道的美国人,但骂得最多的也是这个国家的人;一个美国历史上最繁忙的大作家,除了写书之外,曾做过密西西比河的领航员、新闻记者、排字工人、巡回演讲人、社会活动家、出版商……不过无论如何,丰富而多面的马克·吐温才是最真实的。
他活得就像一出时至今日依旧在上演的经典“美国梦”,只不过现在演员更多地换成了非美国公民的人士而已。在那些纷繁的经历背后,小说创作似乎变成了他人生中“微小”的部分,但他就凭着那“微小”部分中的几部杰作,成为美国文学界最经典的作家之一。在他的身后,无数人承着他的脚步,听着他的笑声而来。有些是同辈,更多的则是后辈们。其中尤为出色的比如福克纳,舍伍德·安德森,海明威,约瑟夫·海勒。他们踏着这个白发老人的脚步,走得更远,不仅延续了他的笑声,更延续了他的梦。
舍伍德·安德森和海明威在文学创作上,都继承了马克·吐温的语言风格和艺术风格,但后者更为成功,影响也更大。海明威在小说中模仿马克·吐温,成功地运用了从中西部方言中提炼出的文学语言,在写作风格上达到了简洁、明快、含蓄的效果。这一风格主要体现在他的“冰山”创作原则上。“冰山在海里移动很是庄严、雄伟,这是因为它只有八分之一露在水面。”所以在创作时海明威十分注重简洁的文风,厚积薄发,给读者留下充分的思索空间,去理解那在水下的“八分之七”。英国评论家赫欧贝茨曾就其简洁称赞说:“海明威是个拿着一把板斧的人,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他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花花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确实,海明威一改19世纪后半期英美小说中句型冗长、形容词多的文风,用电报式的短句,直截了当,简洁凝练,带给人们的是一种直觉的爽快与清新。
福克纳则在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继续探讨了“美国文学之父”在两部历险记中关于孩子成长过程中如何面对成人世界的困惑。如何走向成熟以及对种族偏见批判的文学主题。在《熊》、《烧马棚》、《坟墓的闯入者》、《掠夺者》等类似的作品中,福克纳极大地继承并发展了马克·吐温的成长主题,但同时又有区别,使讲述“成长”的母题在美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支主流。
而后辈约瑟夫·海勒则是20世纪60年代在美国文坛出现的“黑色幽默”小说的代表作家,一部《第二十二条军规》开启了继马克·吐温之后幽默文学史上的新篇章。在他的幽默里,老前辈的印记并不难找,比如混乱的逻辑,主客观的矛盾等。但与马克·吐温代表的美国传统幽默相比,他却又有着本质的区别。就像黑色幽默作家冯尼格所说的那样:“最大的笑声是建筑在最大的失望和最大的恐惧之上的。”所以说,如果前者代表着一种乐观、自信的时代状态,那么后者更多的则是带着消极、悲观、绝望的态度。
所以福克纳说得没错:“以我之见,马克·吐温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他之后的我们所有人,都是他传下来的后代。”
一个伟大的作家永生的生命大概就是这样得到的吧。这么开始,那么结束。他的传奇、梦想、笑声并没有因为肉身的离去而逝去,它们被输进一又一代代人的血液里。于是代代人都成了他的后代。这该是生之为人的最大幸福了。
现在这个幸福的老人已经得到了“最宝贵的礼物”,那我们就不要再打搅他了,要做的只是倾听、阅读、思考和微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