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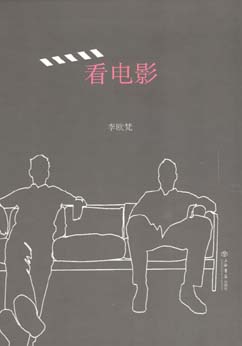 《看电影》(李欧梵著)作为著名的“小32开精装本书系”之一,新近推出。书中,从《小城之春》到《色戒》,从《傲慢与偏见》到《苏丝黄的世界》,作为影迷的李欧梵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观影经历和独特感受。 《看电影》(李欧梵著)作为著名的“小32开精装本书系”之一,新近推出。书中,从《小城之春》到《色戒》,从《傲慢与偏见》到《苏丝黄的世界》,作为影迷的李欧梵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的观影经历和独特感受。
本文摘编自该书。
如果有人问我:中国电影史上最出色的一部电影是什么?
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小城之春》(1948)。这并非我个人的主见,而是研究中国影史的学者所公认。这部影片的导演费穆(1906——1951)死于香港,他的女儿就是著名的声乐家费明仪。但香港影迷似乎对费穆漠不关心,只有关锦鹏在《阮玲玉》一片中特别把费穆变成一个大配角,而且说的是上海话。
我第一次看《小城之春》也和香港有关。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香港举办一个中国三十年代电影回顾展,我正在美国芝加哥大学教书,有幸受邀参加,作为少数的“海外嘉宾”之一。这令我大开眼界,看了二十多部老电影,就此着了迷。
然而《小城之春》并非在参展影片之列。在会议期间,突然有朋友说在某友人家可以看到《小城之春》,于是大家一窝蜂都去了。我一向后知后觉,在电影方面一向走在老友郑树森之后,但却能亦步亦趋,他说好的片子我一定找来看。记得那一晚我就是随着他去的。观后傻了,久久说不出话来,心中不禁感到十分诧异:为什么一位老导演(当时我只知其名而已)在抗战胜利后那样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可以拍出如此优秀的电影?而且表现的艺术感如此“现代”?
据闻中国大陆影界人士发现此片也在同一时候,评论家李陀功不可没。据他告诉我:有一次看某部新电影试片,有人从影库里拿出一部旧片来请他看看,名叫《小城之春》,当时他们连费穆是谁都不知道,看完后李陀也傻眼了,但毫不犹豫地说这是一部大师级的经典杰作!多年后。第五代导演之一的田壮壮也拍了一部《小城之春》,由名作家钟阿城编剧:非但向这部经典致敬,而且几乎每一个场景和镜头都是在模仿原作。两年前我在坊间买到一套此二片的VCD,大家一致的结论是:没得比,还是旧的比新的好。
到底好在哪里?对于一般影迷而言,看老电影必须有耐性,而且要忍受拷贝本身的劣品质,正像听复制的三四十年代的古典音乐唱片一样,需要在当年原始的录音条件限制下重新体会大师们的演奏或指挥艺术,听久了自然会心神贯注,得其精髓,甚至可以想象自己身在现场。看老电影亦然,但更需体会到一点:当年影片的节奏较现今的港产片慢很多!而在古典音乐方面,当年的大师们反而比现在的演奏家快得多。
说了不少废话,言归正传。为什么我那么喜欢《小城之春》?
也许是因为我是学文学的,此片看来就像是一篇短篇小说。即便如此,还是有较小说更惊人之处:片中的“旁白”——犹如小说中的“叙事者”的声音——就是来自故事的女主角,这种“主观”手法,在当年影片中极为罕见,甚至主观叙事技巧本身——一种十分现代的艺术方式——在文学作品中也不多见。“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影响到三四十年代的电影,基本上是现实主义挂帅,用的是客观手法,“全知”观点,甚至原来小说中特意使用的主观叙事者的角色——如鲁迅小说《祝福》中的“我”——在改编成电影时也省略了,好像一盘回锅肉忘了加辣椒,毫无味道。
《小城之春》中,费穆把女主角变成第一人称的叙事者,在中国影史上就是一种创举,因为此片开始时全是两个男人的戏,却由一个女人来叙述,形成了一个很特别的三角关系。原来故事本身的结构就是一场“三角恋爱”,但却处理得如此不俗而大胆。这个女人和她养病的丈夫住在一个小城中一幢破落的旧宅里,片子开始时,却有另一个男人走进他们的世界,原来就是她以前的恋人,而他却又是她丈夫的老友。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好莱坞的影片中,两个男人一定会因妒生恨大打出手,然而中国文化中的情操却是忍让为怀,甚至牺牲。但“小城”亦有“春”意:两个旧情人难道不会有欲望而旧情复燃?做丈夫的又如何处置?
《小城之春》的前半段节奏是徐缓的,却像一首抒情小诗,娓娓道来,如果叙事者换成男人——丈夫或情人——则会韵味尽失。我每看到此处(此片我至少看了不下四五次)都不禁鼓掌叫好,也顾不得叙事者的“文艺腔”了,却更关注片中的背景:这座破落不堪的老房子,真的是残垣败瓦,充满了“颓废”的气氛。此处“颓”和“废”应该分开来解释:八年抗战使得中国变成一片“废墟”,人民元气大伤,片中的两个男人都是典型的知识分子,经过战争和流亡的磨难后,变得十分颓唐,以前的理想破灭了,唯有在一片废墟中休养生息,有待复原。
费穆的伟大之处,我认为就是把这种源自当时环境的“颓废美学”在影片中呈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