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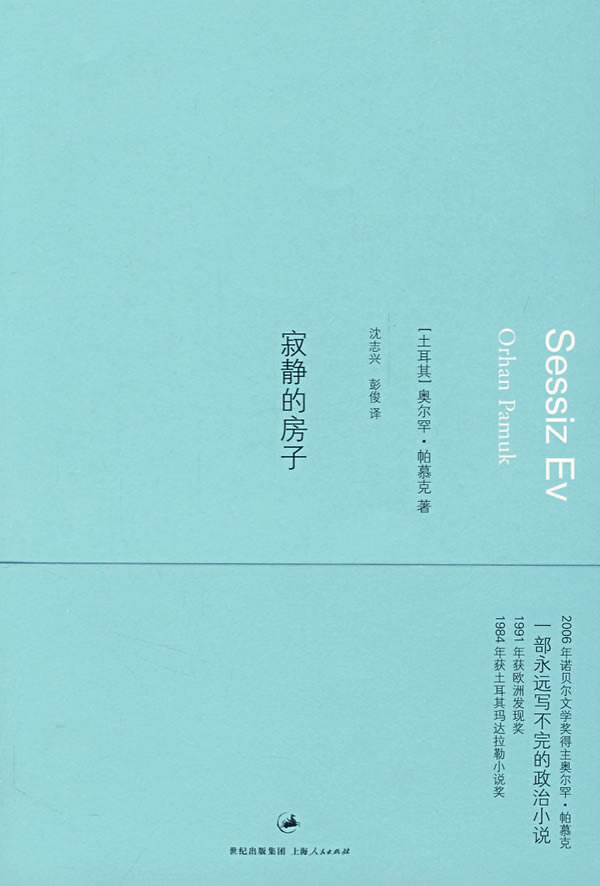 5月下旬,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第一次访华。十天中,他游历了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个城市。9年前,土耳其也发生了地震。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回忆道:“地震时,我在桌子底下摞了几叠百科全书,当中留了个空间。如果发生地震,我就躲进去。我完全了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焦虑无助、悲观。那么多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让我很有负罪感。” 5月下旬,诺贝尔奖文学奖得主、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第一次访华。十天中,他游历了北京、绍兴、杭州、上海四个城市。9年前,土耳其也发生了地震。接受本报专访时,他回忆道:“地震时,我在桌子底下摞了几叠百科全书,当中留了个空间。如果发生地震,我就躲进去。我完全了解人们在灾难中的焦虑无助、悲观。那么多人死去,自己却无能为力。他们死了,而我还活着,这让我很有负罪感。”
5月28日22点,阵雨之后的绍兴,空气新鲜。帕慕克绕着绍兴酒店走了大半圈。此时,没有演讲、采访、签名。帕慕克放慢了脚步,轻柔地踩着地,看起来,没什么力道。同行的中国社科院研究员许金龙说,从帕慕克抵华以来,这种清静很难得。
7天前,帕慕克和女友、2006年布克奖得主基兰·德赛抵达北京。这是帕慕克第一次来到中国内地。
应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的邀请,帕慕克在北京、绍兴、上海进行为期十天的访问。自帕慕克200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出版其中文版小说的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就想方设法欲邀请他来华。2007年3月、8月,坊间数次传出帕慕克即将到访中国的消息。但因为帕慕克受到土耳其国内极端民族分子的死亡威胁,流亡国外,导致计划全部泡汤。今年3月,一场以帕慕克为头号暗杀对象的密谋被破获,参与密谋行刺有13人,其中3人被警方逮捕,现已开庭审理。帕慕克说,为了保护他,他家直到现在还有警察站岗,“在土耳其等一些高压政策的国家里,敢说真话的作家肯定会受到生命威胁。但作为普通人,我希望有生活的权利,我不怕,我只想写作,写出自己的想法。”
如今,帕慕克一年有四个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上课。他说教书权当旅游,日子先这样凑合着过。
刚到中国,在表达完对四川地震灾区的同情后,帕慕克就急不可待地说:“在北京这几天,如果时间允许,我想参观博物馆,特别想看中国的传统绘画,我是中国绘画的fans。相对西方绘画来说,中国绘画是另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
5月26日晚,在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对帕慕克的私人宴请上,有学者对他说,你了解细密画,但不了解中国绘画。帕慕克回答,此次中国行,就是来补课的。他几次对铁凝说,会把中国元素融入自己的作品里。
“我喜欢旅行,旅行总能给我各种各样的想法”,正如以往每次为写作去各地搜集素材一样,帕慕克的中国行也是有备而来。
缺席自己作品的研讨会
到中国下了飞机,帕慕克对他的中国之行的陪同许金龙说:“我就是一个大孩子。”
5月24日中午,帕慕克在北大附中四楼学生食堂里吃饭。饭前,帕慕克和食堂大厨学包饺子。
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两次为帕慕克设宴,一次在宫廷菜馆仿膳,一次在茉莉餐厅。帕慕克好奇于老北京点心“驴打滚”如何滚起来。见到好吃的点心,他动手就拿。
姚映然是《我的名字叫红》中文版责任编辑。以前读帕慕克的作品,姚映然觉得他是一个羞涩的人。但见面后的感觉完全不同,“他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写作精准,思辨逻辑力强,很有控制力,但对日常生活特别感性,一发现喜欢的东西,就会特别开心,像小孩一样。如果反感,就会一下子消沉,转身就走。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
帕慕克满头花白头发,笑起来,一脸狡黠。他平时不喜欢应酬,也不爱出席派对,甚至没什么朋友。以正常成年人的标准看,他不世故不圆滑,开心与否全在脸上。有朋友说帕慕克“奇妙地结合了文学天才的智慧、孩子气的天真幼稚”。
5月23日,为期一天的帕慕克作品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社科院举行。当年大江健三郎访华时,其作品研讨会也在这里举行。
帕慕克和大江是朋友。但是,帕慕克在研讨会上的表现和大江健三郎完全不同。研讨会开始前,帕慕克就自己的写作经验做了20分钟发言。讲话结束前,他出人意料地说:“对我的作品有很多不同的解读。我的作品里也有非常丰富的材料可以让大家进行不同的解读。每当我听到不同的解读时,我都觉得这些解读者在阅读我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我想隐藏起来的。所以当面听大家的解读,对我来说,有点困难。”说完,帕慕克便离席而去。与会专家学者面面相觑。研讨会在帕慕克的缺席中进行,下午3点就提前结束。
有学者指责帕慕克“无礼”、“随便”。人们拿他和当年的大江健三郎相比,“大江毕竟是苦孩子出身,随和”。
也有学者为帕慕克辩解。中国社科院外文所副所长陆建德说:“帕慕克本来就不想参加研讨会,我们尊重他的决定。钱钟书也不喜欢参加研讨,吃鸡蛋没必要认识下鸡蛋的母鸡。”副研究员侯玮红猜测,帕慕克的离席是“因为害羞”。
在世界范围,帕慕克几乎不出席自己的作品研讨会。在去年6月由土耳其文化和旅游部举办的首届文学国际研讨会上,两天的会议中安排了半天讨论帕慕克的作品。帕慕克也没有出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