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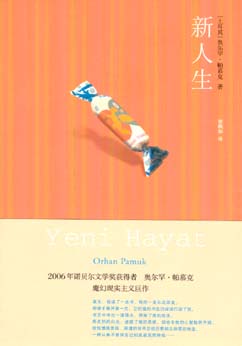 身处两难困境,生存在不东不西,不土不洋的夹缝地带,被 身处两难困境,生存在不东不西,不土不洋的夹缝地带,被
催逼,被呵斥,被推搡;现代要把你拉走,传统却拽住你不放;政治驱赶着你,时刻提醒你注意后颈的冷枪,艺术却让你忘记脚下,只看向高远的地方;还有冷冰冰的宗教世界,以及五彩的世俗生活,各自在你身上,展现着针锋相对的力量。
谁会喜欢这种困境呢?奥尔罕·帕慕克——土耳其文学的代言人、2006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几天前在北京告诉读书报记者:“这种两难的境遇构成了我的故事,它是我幸福的源泉。”
为灾难而感到内疚
帕慕克初抵中国的首日,正是中国人民为四川大地震遇难者设立的全国哀悼日第三天。他深知地震带给人民心灵的巨大冲击,在访华行程中,他多次谈到地震,不仅表示了痛惜之情和慰问之意,亦回忆起1999年土耳其地震期间他自己的特殊感受:“我知道地震意味着什么,知道人民有多难过,国家有多么悲痛。”
1999年8月17日的土耳其地震,夺去了三万人的生命。帕慕克在伊斯坦布尔所住的小岛,距离震中仅有25英里,第一次震动持续了45秒,却带给他内心更为长久而深刻的震撼。他先后写下两篇关于地震的文章,皆收入即将出版中文版随笔集《别样的色彩》中。
“地震离我如此之近,带走了如此多的人的生命,我简直无法面对这个事实。”帕慕克写道,“它摧毁了我度过了大部分童年的地方,这种难以置信更让我感到恐惧。”
几天后,他渡过海湾,到了对面受到强烈破坏的震区:“我们一个一个房间地徘徊,目瞪口呆地望着其中暴露的一切,这另一面让我们看到了生活的脆弱,面对恶魔的杰作,人们是多么无能为力……一条街又一条街,我们走了很长时间,感到灾难对历史和我们心灵的改变永远不会结束。”
5月22日,在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发表演讲之后,帕慕克反复提及了自己在地震之后的“内疚”感受。在书中他也是这样写的:面对灾难,作为他这样的活着的人,那种“自我保护的愿望”十足令人难堪:“虽然人们很少说起,但它有时能从很多人眼中看出。我把它称作是一种羞耻感,一种夹杂着些许内疚与自责的羞耻感。”地震后,他几乎断绝了与一切人的来往,“就像一个刚被诊断出罹患了癌症的人,首先想到的就是不要让任何人知道。”
“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
今年2月,中华读书报曾刊出长文《保卫奥尔罕·帕慕克》,提及他所面临的三重威胁:因为公开评论亚美尼亚人大屠杀事件而被控“侮辱土耳其国格”的未完结的法律诉讼,极端民族主义分子针对他的暗杀计划,以及某些评论家至今就他因“政治原因”才获得诺贝尔奖垂青的喋喋不休。那么,面对这些威胁,他怎样保护自己?对读书报记者的这个问题,帕慕克再三强调要拿作品说话。在来中国之前,“我刚刚写完了一部600页的小说。”他说。他指的应该是那本传闻已久的《清白博物馆》。“我很高兴能借此向世界证明,诺贝尔奖金绝非退休金。”他志得意满地说道,“我的书已被译成了56种语言,我的书也会流传下去。”
帕慕克作品的中译者沈志兴对读书报记者谈及自己对这位大作家的感受。“性情中人。”沈先生说,“喜怒形于色,但也不乏幽默。”
有位记者同行向我描述了“老帕”在北京期间因一位摄影师干扰而动怒的场面。但帕慕克给我留下的印象,好过此前人们对他不苟言笑、书呆子,以及缺乏幽默感的描述。他的个头比我想像中更高,一头栗色头发也几乎完全灰白。
2007年,帕慕克曾告诉朋友:“因为我对原教旨主义者的恐惧,我不得不与保镖一起旅行。时刻与他们在一起的日子是不值得过的生活。”但是,此番他来华访问,始终未见保镖踪影。他笑着说:“中国是最安全的地方。”
风光东亚行
帕慕克这一趟旅程着实不短,几乎可称“东亚一月游”。他先去了韩国,继而日本,然后中国。所到之处,则是大量的演讲、座谈、签售和游历——他喜欢美术,乐于拜访中、日、韩的美术馆和博物馆,还要接受无尽的采访。
不久前,另一位诺贝尔奖得主、英国女作家多丽丝·莱辛公开抱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简直是个“大祸害”,弄得她根本没法写作,而把无尽的时间用于应付拍照和接受采访。帕慕克倒没这么极端。在韩国接受当地《中央日报》的采访,他被问及这一问题时的回答如下:“我跟人们开玩笑说,诺贝尔奖如何扩展了我的银行账号和电子邮件的账号。别看有作家抱怨,但我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井井有条。我刚写完了一本600页的书。我比得奖前更努力工作。我在一个相对年轻的年龄得到了诺贝尔奖。”
是啊,现在他还不到56岁,而莱辛女士已经88岁了。
他在韩国赞美汉城的高楼,在日本向谷崎润一郎致敬,到了中国,则反复提及《红楼梦》和鲁迅,但也仅仅是提及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