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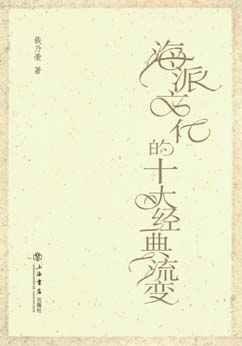 题记 题记
去钱乃荣教授家拜访的日子,正赶上他即将启程前往荷兰参加“中国和欧洲工业化:语言接触和认同”会议的前一天。这位一生和上海话结缘的老教授,坐在一堆手稿和多年来搜集的中外上海话著作中,为即将面世的三本著作作最后的审订工作。今年8月15日举行上海书展上,除了最近备受关注的《上海话大词典》外,钱乃荣的《上海方言》、《海派文化的十大经典流变》同时与读者见面。
近年来,海派文化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上海话大词典》却迟迟没能出现。面临上海话在传播中只能说不能写的窘境,钱乃荣教授开始了当时看来完全没有底的工作。
编《上海话大词典》这项琐碎的工程,您没有让研究生帮忙一起弄吗?面对记者的提问,身为上海大学语言研究中心主任的钱教授道出了自己的苦衷,“我已经好多年都招不到热衷于阿拉上海闲话的研究生了。不仅是我们学校,复旦、华师大等都招不到这方面的研究生,越是发达的大城市,越招不到坚持研究本地语言的人。”
“很奇怪的是一些身在海外或学理工科的年轻人,似乎比身在上海或文科毕业的同龄人更认同自己的母语,对上海话有着异乎寻常的感情。”钱教授告诉记者,“他们已经行动起来了,他们用上海话Rap,用上海话写作,办上海话网站,他们或许不是那么严谨,但他们玩得那么开心,他们让上海话重现活力。”钱乃荣说他闲暇时会经常去逛上海闲话和吴语方言网站,跟年轻人“谈谈山海经”。他说:“香港八所大学,六所开设了上海话专业,‘第六代’导演贾樟柯一直使用山西演员和山西话拍电影,语言必须要在传播中不断创新才有生命力。”
第二次采访钱乃荣,他已从荷兰回到上海。他十分激动地告诉记者,在荷兰的会议上,国家语委副主任李宇明作了“中国语言规划进入第三阶段——建设和谐的语言生活”的主题发言,提出了要“树立语言资源观念,珍爱人类的语言及其方言”,“通过功能规划使各种语言各按其位、各得其用、各展其长”。“这是多么重要的信息啊!”钱教授一再表示希望将这令人振奋的信息,通过本报传递出去。
跟钱教授聊编词典的同时,记者的注意力也被另外一些东西吸引住了。时近黄昏,钱教授家书房里的那只老式唱机和那只怀旧的彩色玻璃台灯,在暗淡的光线中放射出旧时的光彩。这只唱机是一进门就看见的,如今的上海人家里,已经很难看到这种喇叭大大老式唱机了。
终于,记者忍不住要求,“能不能用它放一放您收藏的那些宝贝?”钱教授低头一笑,“没问题啊!”他小心翼翼地拿出收藏多年的200多张78转老唱片,一一展示给我看。从上世纪30年代百代公司出版的黎锦晖词曲、黎明晖演唱的《毛毛雨》,胜利公司出版周璇演唱的《特别快车》、黎莉莉演唱的《桃花江》,到第一代滑稽演员王无能、陆啸梧、徐卓呆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行的唱片都有。从小热爱上海、热爱上海话的钱乃荣,当然特别钟爱海派文化。收藏的不少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老歌、滑稽戏唱片,钱教授一遍遍听,久而久之都已经能唱能说。钱乃荣告诉记者,前两天上海著名的滑稽演员王汝刚的儿子来家里看他,见到这些货色,啧啧称奇,说“就连上海滑稽剧团的资料库里都不见得有!”
对海派文化的喜爱,同时也加深了钱乃荣对沪语的认识。“你知道吗?第一、二代滑稽戏演员陆啸梧、江笑笑的滑稽戏里,很多都是讲苏州话的,但是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左右,就是以上海话为主、苏州话为辅了,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的滑稽其实受‘苏滩’的影响很大”,钱教授告诉记者,“方言研究,就是要从事实出发,用事实来说明问题。上海话紧紧扎根于海派文化之中,从中可见端倪。”
说着,钱教授在众多老唱片里抽出一张“百代唱片”出品、周璇演唱的《何日君再来》,放进那只老式唱机中,拨动唱针的同时,“金嗓子”委婉动听的唱腔飘了出来,沙沙的黑胶老唱片隔着时空,却一下子将蛰伏着多少恨,多少爱,多少失落的往昔年代重现在眼前。
除了老上海的流行歌曲、滑稽戏,钱教授的藏品还包括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越剧演员施银花、筱丹桂、马璋花、姚水娟等的唱片和沪语唱片,和另外一些意想不到的藏品——花花绿绿的糖纸头。钱教授收藏的糖纸有厚厚几大本,糖纸面上有各生产厂家的名字,如伟多利、天明、冠生园、益民、大众;还写明糖果的种类,大多用的是西文的译名,如太妃(toffee)糖、牛轧(nougat)糖(又译成鸟结糖)、求是(juice)糖、白脱(butter)糖等等。钱教授告诉记者,上世纪50年代是糖纸头水准的高峰期,著名的连环画家戴敦邦、贺友直等,当初也曾加入设计糖纸头。作为商业文化的代表,这支奇葩开得如此鲜艳。上海书店出版社正在计划,在下半年为钱教授家的糖纸头出一本书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