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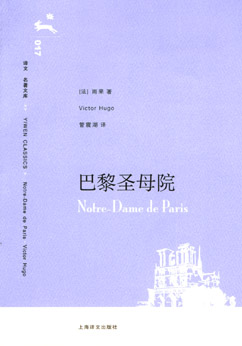 ■ 黄金屋里颜如玉 ■ 黄金屋里颜如玉
看《巴黎圣母院》,女一号爱斯美腊达始终如雾中花,色与香都隔着人一层,隐隐约约都在那里,却既看不仔细,又闻不真切,在上达国王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的风俗画卷里,显得苍白而抽象。她是叙事内外所有视觉的焦点,读者与每个叙述中的人物一起观察她、评估她,所有的视线在她身上聚焦成强光。在强光下,她却只是一个模糊的影子。她像一面镜子,读者透过她,可以观察小说中所有的男性,但如同镜子一般,她自己却只是一层不可穿透的冰冷平面,纯粹,莫测,印证罗塞蒂的诗句:女人不是作为她自己,而是作为男性之梦而存在。
爱斯美腊达是小说中所有男人的梦。小说开头,美女尚未出场,就将广场上狂欢群众的魂魄夺了去:“……真跟耍魔术似的,大厅里剩下的人全都冲到窗口,爬上墙头,向外张望,叨叨着,爱斯美腊达!爱斯美腊达!……”人群敬之如女神,惧之若女妖,整个乞丐王国爱戴她,曾与她“摔罐成亲”的流浪诗人格兰古瓦倾慕她,御前侍卫队长孚比斯亵玩她,然而,这些与她扯得上表层关系的人物并未在真正意义上接近过她。对于爱斯美腊达那近乎神性的美,他们也从没机会徐徐打量,细细鉴赏。乍看去,整个巴黎好像是一座巨大的拍卖台,吉卜赛女郎爱斯美腊达便是台上那件既灼目又烫手的无价之宝。觊觎的不少,真正敢喊价的却不多。
芸芸众生里,只有两位真正的“鉴赏家”。副主教克洛德·弗罗洛凭着他的地位、知识和权力,得以从至高处俯视她;敲钟人卡席莫多则被自己的相貌和出身贬到了生活的最底层(世俗的目光几乎剥夺了他生而为“人”的权力,他更像是一头畸形的动物),因此只能从极低处仰视她。至高和至低是极险峻的视角,是透视的端点,能见人所未见。要将窥测目光穿越女性那“镜子”般的表面,那是最具可能性的位置。所以这一双男性目光,抽象凝聚着千古所有男性对女性纯粹的鉴赏眼光——抛开善恶判断标准,某种意义上,只有他们才真正懂得爱斯美腊达的女性美。
但处于至高者,众目睽睽之下,却受限于男性社会的禁制规范,位在最低者,缺乏猎取女性对象的基本条件,两者都失去成为“购买”或“收藏”者的潜在可能性。最具鉴赏眼光,却最无猎取能力,这两面所构成的张力,把他们的渴望逼迫到无以复加。
小说演至高潮,卡席莫多从刑场上救下爱斯美腊达,藏进圣母院里供犯人避难的小屋,与欲将其置于死地的克洛德展开决战。珍宝惟此一件,一方面是“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伤害(染指)你”,一方面是“我得不到你,也不让别人得到你”。爱斯美腊达之死,固然是克洛德主观上步步陷害的结果,客观上却也因为卡席莫多护佳人心切,乃至误解乞丐王国的营救计划,继而阴差阳错地换来了国王宣判的死刑令。极端纯粹的对女性的“审美”态度,最终“合力”把他们恋慕的对象击成碎片,他们本身也一同毁灭。这实在是富有启示录般象征性的情节。
对于女性美的极度审视,必然引发收藏这种美丽之物的极度渴求,但这种渴求,终将在男性社会的规制下被湮没——制度单只允许平庸者的寻常需求。爱斯美腊达作为一个完全抽象的个体,却成为全部女性美的象征,谁敢于把“她”收藏到自己的名下,必将冒犯众怒,受到制度的毁灭性镇压,因为“制度”本身就为权衡众望而设。
这两个处在极端位置的角色真正撑起了小说的灵魂,也在某条隐性的文学长河里竖起了两根绕不过去的木桩。读《洛丽塔》,读者在那个将少女先驯养后虐杀的亨·亨身上瞥见了克洛德的魅影;看《香水》,观众在萃取少女体香以使其“永生”的格雷诺耶身上嗅到了卡席莫多的气味……一切真正穿透女性美那镜面般深邃的男性目光,视角无论于高处低处,都将至于毁灭。就这一点而言,亨·亨之于克洛德,格雷诺耶之于卡席莫多,算得上是隔了遥远时空的貌离神合的远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