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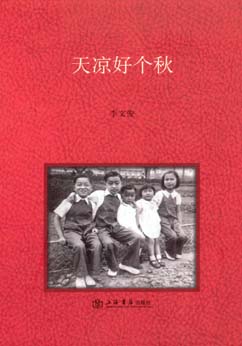 有一回,马尔罗问梅纽因:君于音乐所常感受者为何事?梅答曰:“乡思(Nostalgia)。欧洲音乐钜作莫非忆恋失去之乐园而歌也。”(钱锺书先生译文)。这句话正好说出我一口气读完李文俊先生《天凉好个秋》后的感受。我爱这本“回忆随想曲”,因为里面没有一句假大空套话,没有“罗生门”式的自我炒作,记载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者在上海法租界里度过的童年岁月,由于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因此读来更觉字字亲切、句句朴实。正如作者引用布莱克的诗中说的,你往往能从一粒沙子、一朵野花里窥见整个世界,把握无限和永恒…… 有一回,马尔罗问梅纽因:君于音乐所常感受者为何事?梅答曰:“乡思(Nostalgia)。欧洲音乐钜作莫非忆恋失去之乐园而歌也。”(钱锺书先生译文)。这句话正好说出我一口气读完李文俊先生《天凉好个秋》后的感受。我爱这本“回忆随想曲”,因为里面没有一句假大空套话,没有“罗生门”式的自我炒作,记载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作者在上海法租界里度过的童年岁月,由于我也有类似的经历,因此读来更觉字字亲切、句句朴实。正如作者引用布莱克的诗中说的,你往往能从一粒沙子、一朵野花里窥见整个世界,把握无限和永恒……
我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刺刀已近在咫尺,小学生们仍在高唱《中国不会亡》;邻家男孩因参加抗日活动被日寇追捕,逃入李家,李母梁冠英女士,一位普通的家庭妇女,顷刻间作出生死抉择,冒称那男孩是她的大儿子,使这位少年爱国者得救……,这使我记起,在整个沦陷时期,我所接触到的老师、同学、亲友、邻里,绝大多数都深明民族大义,大家最关心的是抗战的前途,关心守卫四行仓库的谢晋元团勇士们的命运,就连小朋友们头脑中也充满岳飞、文天祥的英雄事迹……我想,正因为如此,中国才真的没有亡。
作者童年趣事读来非常亲切有味:三五岁时他就独自溜到教堂门口去索取宗教宣传品。散发材料的那位女士说:“侬小人看勿懂格!”不料这名小广东竟会振振有词地说:“拿番去被我姆妈睇!”……长大,上学,淘气异常,曾被美术老师钱君匋赏以“毛栗子”;他也真有福气,晚年撰文述及此事,钱师见了,还赠以墨宝。他还记得钱师念贝多芬为“Bee拖粪(上海话的‘拖把’)”,因此这一名字常会使他联想到“清洁卫生”;他和隔壁弄堂里的小朋友们玩“刮香烟牌子”,被他们用不正当的手段统统赢走,他正在哭,大哥慷慨地拿出一大叠香烟牌子相赠,尽管香烟牌子墨黑,上面不知沾有多少细菌,但事隔七十载仍令他感念不已……像这样富于幽默、充满感情的文字,不由地使我想起狄更斯的叙事风格,果真如此,我看到作者在书中说起,他少年时曾读狄更斯入迷……
作者李文俊先生是翻译大家,是我的学长,是上海位育中学第一届毕业生(五年一贯制)。如今位育已是市重点名校之一,其实,当年教学质量之佳远非往后可比。许多骨干教师49年后都去大学任教。书中提到他曾聆听陆福遐先生在位育的第一次英语讲演,陆先生风趣地说,英语“don't you see”发音就像上海话“大曲死”。陆先生也是我的恩师,他生性幽默,温和善良,五十年代中期,他调往上海外国语学院任教,在运动中遭了难。“文化大革命”前,他与我最后一次见面时,还告诉我说,他著有一本《中国学生英语典型错误分析》,但他是不能署名的。位育毕业生中人才辈出,据曾任位育训育主任的朱家泽先生说,光是大学校长就出了28名之多。我不知道他的统计数字中是否包括前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记得田长霖学长曾说过,他在位育读书时,并不是学习尖子,他后来有所成就,只是“成才的环境不同”而已。在这里,我倒要提一提位育真正的学习尖子之一沈元,郭沫若在看了沈元23岁时写的《〈急就篇〉研究》后说,这么好的文章,“我写不出来!”(参看《炎黄春秋》2006年第五期/刘志琴文)
作者提起他和老伴、德语文学专家张佩芬游巴黎时,在一处幽静的小巷,忽然有重回当年上海法租界的感觉。这很自然,中国之大,发展不平衡,太平洋战争前的上海是远东金融中心,局部地区确实已经相当文明,相当现代化了。当时我们所在的地段,街道非常干净,人们也留意自己的行为举止,很少有人会随地吐痰,更不见“城市牛皮癣”,是日本的野蛮侵略,阻止了我国逐渐进步的过程……。书中提到作者以及他的哥哥、姐姐是如何与音乐、文学结缘、亲近的……邻居家的几个哥哥进了圣约翰大学,不久就像换了个人似的,一举一动都斯斯文文,说话不但无脏词儿,连“侬”,“阿拉”也少用了。作者说,街道整洁、环境幽雅、建筑精致,有利于小孩心灵与艺术趣味的发展。信哉斯言!可惜在往后的岁月里,这一切都以“小资情调”、甚至“洋奴意识”的严重罪名遭到批判,另一种文明观占了优势,以致今天还要向成年人倡导幼稚园小朋友也该懂得的行为规范。也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海峡两岸的影视界忽然都“乡思”病大作,都爱以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滩”为背景制片,但坦白地讲,这些作品里找不到当时生活的神髓精魂,“情调”和“品味”这类东西好奇怪,打碎它容易,但培植起来,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做得到的。作为曾在当时当地生活过的人,往事恍如一梦,只是在阅读《天凉好个秋》时,才能捕捉到一些记忆的碎片。那么就回忆吧!让·保尔不是说过吗:“回忆是我们不会被逐出的惟一天堂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