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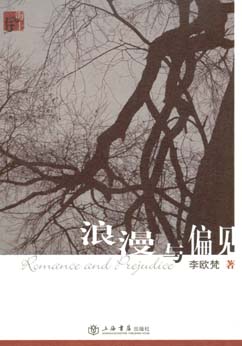 看李欧梵先生写的康桥和志摩——两样都是我钟爱的话题。 看李欧梵先生写的康桥和志摩——两样都是我钟爱的话题。
志摩的康桥是1920年代。那个春天他不过二十三四岁,刚离婚,独自一人在王家学院做一个既无经济压力也无学习压力的特别生,每个清晨和黄昏,就痴坐在青青堤岸上,对着长满水草的康河抒情。后人多少应当感谢徐志摩,若不是当年他在康河畔留下的那些文字,剑桥的美色或许就会在一个匆匆的“英国五日游”里被忽略了;也自然不会有那40多年后李欧梵的漂洋过海。
1968年的夏天,还在哈佛大学读书的李欧梵到英国收集论文的资料和灵感——其实,论文只是个堂而皇之的借口,他到康桥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徐志摩”。彼时,小李先生也不过二十来岁,也处于“耐寻味”的单独中,也有着一腔的热情和诗情,要去发现康桥的真。凑巧得很,那正是英国最好的季节,“荒谬的可爱”,康桥的美色和灵性四处漫溢,四十年如一日的绚烂,没有多少六十年代的痕迹——从某种意义上讲,今天的康桥也没有二十一世纪的痕迹,康桥是没有年纪的。
在康桥你是无须恋爱的,因为那风景便是你最好的情人;所以徐享受着他蜜甜的单独,那个一生中唯一没有虚度的春天。在康桥也是可以恋爱的,恋人的眼睛是康桥美景的更好点缀;所以李写下了一段与瑞典女子的浪漫邂逅。李欧梵的这一篇文字,主人公用的是“他”,却又声明是真实的非虚构,读来真真假假,让人起疑,难免做暧昧的猜测。叫人疑惑的另一点是,中国男子面对金发美女时大多怯场,怎么李居然有这样主动搭讪的勇气。
后来,读到李先生的另一段轶事,说他在念研究院的时候,常去舞会,且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随着音乐手足摇摆舞将起来,一舞之后如双方不弃则再舞,当跳到慢步舞的时候,就可以把脸贴上去,舞后问她电话号码,牢记心中或写在电话本上,以备不时之需”。又找到刘绍铭先生对于李氏浪漫情怀的解释:原来浪漫一词出自苏轼的“年来转觉此生浮,又作三吴浪漫游”。浪漫本来就有任意、洒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含义;而浪漫精神强调感情自然流露,“浪漫主义者谈情说爱也比古典主义者轰轰烈烈、多彩多姿”。读到这里,豁然开朗。浪漫者需要勇气,这恰是李欧梵内心充沛的地方。
那康桥的十来天,成就了一个浪漫主义者对另一个浪漫主义者的追寻,并最终落下了浪漫不羁的文字,做了这本学术散文集《浪漫与偏见》的开篇——这实在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也应合了《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那句话:我这一生的周折,大多寻得出感情的线索。
徐志摩之后的篇章,从纽约到布拉格,从哈佛到香港,从哈维尔到卡夫卡,从张爱玲到胡金铨,都是李欧梵先生真性真情的流露和轨迹。而所谓的“浪漫与偏见”,则是卸下了哈佛大学教授的头衔和学术著作的威严之后的畅所欲言;这样的散文极其对我的胃口,就像看亨德利沙立文们脱去衬衣马甲、换上T恤后进行斯诺克比赛,有着闲庭信步式的驾轻就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