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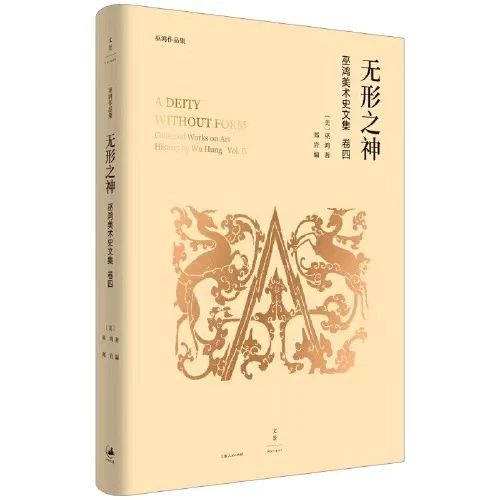
《无形之神》
[美]巫鸿 著 郑岩 编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景
虽然许多内容丰富的学术专著与文章已经对敦煌艺术进行了讨论,但它们研究的基本都是敦煌艺术中的一个特殊现象,即莫高窟千佛洞中留存下来的佛教艺术品,而非作为一种整体视觉文化的“敦煌艺术”。换言之,对于敦煌艺术的研究,我们更多地注意到的是我们之所见,而非古人之所见。我们是否能更好地利用历史遗留下来的资料,来重构敦煌艺术的历史视角?这一重构需要如何进一步努力,又面临着何种方法论的挑战?本文将通过探索敦煌艺术的内容与其地理空间的复杂性来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通常不加思考地把敦煌艺术等同于敦煌的佛教艺术。这个概念上的模糊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我们心甘情愿地被莫高窟中辉煌的壁画与雕塑所吸引和震撼。但是这个概念上的模糊有着相当严重的后果,它阻碍了我们理解敦煌艺术的全部内容,也因此暗中遮蔽了敦煌佛教艺术的历史原境。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需要认识到敦煌是一个实际的文化地理环境,而莫高窟——一个位于敦煌南端25公里处的佛教建筑群——只是这个文化地理环境的一部分。在中古时期,敦煌城内城外有着多处宗庙和礼仪建筑,不仅有授习佛教和礼拜佛陀的场所,也有道教、儒教、祆教以及地方宗教和祖先祭拜的地点。我们需要理解这种多中心视觉文化的社会条件:中古时期的敦煌是一个移民城镇,居住着来自不同地区、具有不同宗教信仰与文化传统的人。因此敦煌的佛教艺术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艺术传统,要理解它的历史意义,就必须把它和彼时彼地发展起来的其他文化和视觉传统联系起来。
今天,从敦煌城前往建于三危山崖面上的莫高窟参观,先要穿过一片广袤的沙漠。实际上,这个区域从3世纪开始就一直被当地居民作为墓地。
通过过去60年的考古工作,人们已经在这里发现了约1000座西晋至唐代的墓葬,而更多的墓仍被沙漠掩埋。这些墓葬的断代十分重要,因为它们的时代意味着这处墓地的存在与邻近的莫高窟几乎是平行的。莫高窟中最早设立的佛教圣像与墓地中的早期墓葬的时代相近,而这些墓葬中发现的是道教的镇墓文和为死者无形的灵魂设立的空帐。
我们希望知道:为什么敦煌石窟和墓葬的装饰使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视觉语言?这两种视觉语言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这种关系对理解作为整体的敦煌艺术极为重要,特别是由于越来越多的莫高窟石窟是被作为“家窟”——即一种家庙或家族祠堂——来修建的,其中栩栩如生的壁画把已故的家族成员描绘成来世崇拜佛祖的信徒。传统祖先崇拜中长期存在的二元论——集合性的家族宗庙和家族成员个人墓葬的并存和互补——仍然为敦煌地区佛窟与墓葬的相对关系提供了一个总体的框架:修建在居住区域附近的墓葬为人们提供了死后的居所,而三危山上的“家窟”则在佛陀的祝福下庆祝家族的永远繁盛。
因此,理解敦煌艺术内容及其地理空间之复杂性的方法,首先是确定这一地理空间内的多种宗教和礼仪中心。在中古时期,这些中心也是最重要的公众活动与艺术传播的场所。虽然除莫高窟外这些宗教和礼仪中心无一幸存,但敦煌“藏经洞”中发现的遗书提供了有关它们过去留存状况的珍贵记录。研究者可以通过这些集中于8世纪至10世纪的文献记载,识别出大约20处敦煌的佛教寺院。城中的大型寺院在佛教活动的组织中扮演了主要角色。敦煌遗书中的寺院财产账目列有相当多的雕塑与绘画作品,小型寺庙经常则由个人赞助。大英图书馆收藏的一份珍贵的敦煌遗书(编号S.3929)赞美敦煌画家董保德将自己在城中的居所改造成精致的佛寺,这份文献还记录了董保德和其他供养人合资兴建五座石窟的功德。
董保德是敦煌当地画行中的一名“都料”(主管设计、施工的人员)。10世纪的敦煌遗书也记录了一个敦煌官府画院的情况,其中的画师被分成不同的等级,包括画院师、知画手、院生等。这些官方和民间的画师和被称作“画匠”的一般画工不仅负责装饰佛教寺庙,也绘制祖先画像以及儒家圣贤、道教与祆教的神像。董保德就以擅长绘制肖像画而负盛名。第4640号敦煌遗书中还记载了专业画师被指派去绘制钟馗像的事例。
从敦煌遗书中我们还可以知道至少11座唐代敦煌道观的名字。其中的紫极宫建于公元739至741年间,正是唐玄宗颁布诏令在首都和各郡县建造供奉老子的道观的时期。郡府所在地的这种道观被称为紫极宫,其中设有官方下令建造的老子的“真容”[图53.7]。道教在敦煌的流行至少持续到10世纪以后。敦煌遗书中包括至少649篇道经,另外还有400多篇是道教的曲子、诗歌、医药、天文和各种占卜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