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说起来,本书是在美国一九七五年英文版出版之后十一年才引进中国大陆的,第一个译本是一九八六年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雷格泰姆音乐》。译者是陶洁女士。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八七年,我们的译本由花山文艺出版社推出。虽然该书出版后引起文学界的关注但并未引起很大动静。一九九六年译林出版社在该社总编辑章祖德先生的主持下又把此译本以《拉格泰姆时代》为名收入“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丛书”再次出版。
这样薄薄的一本美国小说居然能够在译本初版九年后再次出版,对于我们这种习惯于坐冷板凳的外国文学翻译者付出的辛劳的确是莫大的鼓励,这不止是我们利用编辑或教学工作之余的辛勤劳作,而且是付出心血之作,对于我的合作者刘国云先生其实更是付出丫生命的代价,抱病翻译,此书竞成为他文学翻译生涯的绝唱,匆匆的离世也使他未能见到一九九六年的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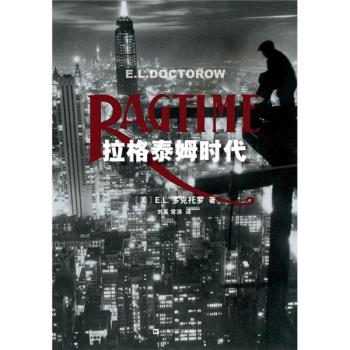
“美国后现代主义文学代表作丛书”的出版在文学界当然是被称道重视的事件,但是对于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生存与发展的大众,所谓严肃文学毕竟属于奢饰品,因而它如果湮没于泥沙俱下的滚滚书潮之中,自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不过,出乎我的意料,在距第二次出版近十八年之际,九久读书人公司的彭伦先生居然通过新浪微博找到了我,表示要重新出版这部小说。
在作为自己归隐之地的面朝大海的房子里,在阅尽三十年人间沧桑之后重新审视这部译稿,我再次为作家E.L.多克托罗这部小说对历史宏观与微观的把握之准确,理解之深刻感到惊讶。回看它在中国虽未能致洛阳纸贵,却能使细水长流的出版史,我忽然明白了它为什么有这样的生命力。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像嚼一枚橄榄,读后回味无穷;如果像一面镜子,令人从中照见迷离现实的真相;如果像一支乐曲,令人感动,与之发生共鸣,它就一定会弥久常新。
重读它,忽然感到一百年前那个充满希望同时又危机四伏的美国,与我们的现实竞有几分相似:怀着美国梦寻找机会的犹太移民,为追求生而平等铤而走险的黑人音乐家,在疯狂奔驰的时代火车驱使下发生的社会巨变,美好与丑陋,繁荣与贫困,发展与风险,彼此交织纠结,似乎天天在上演的复杂剧情,就发生在眼下身边。
想到此,不由得为出版于一九七五年的这部风格独特的美国历史小说有这样的远见而折服,也感谢国内二十七年来三次推出此书的出版者的独具慧眼。
常涛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