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多克托罗,这位20世纪后半叶美国伟大的犹太裔小说家,以其毕生才华作出了两个选择:在现实主义的海岸扬起新历史主义的风帆,以后现代的虚构观念想象城市生活的密度质感。约翰·巴斯曾感叹,一个后现代主义的袋子竟能装进如此多风格迥异的作家。多克托罗被装进去不是因为他不好好讲故事,也不是因为他会玩文本迷宫的小游戏。他像一个幻术大师做着混淆历史与虚构的精彩演出。这不就是在历史与小说中和稀泥吗?不,只能说,虚构是一种姿态,它想象着更高的真实。
多克托罗是城市生活的歌者,小说集《诗人的生活》所收短篇,带着摇摆乐的短促力度、蓝调的无名忧郁、爵士乐的荒野强力,与《纽约兄弟》《世界博览会》史诗般的交响调度形成鲜明反差。同名小说《诗人的生活》并不“好看”,因为叙事者抛弃故事,没有线索,靠搜集其他夫妇的琐屑素材堆砌自己的婚姻空间。作品无序混乱的形式正是对中产阶级空虚生活的戏仿。《流浪汉》初看会以为作者大搞行为艺术,在谋篇上拼贴、剪切、连缀等技法层出不穷。动机却只有一个:用手法暴力造成故事断裂,拆解中产阶级自我放逐的执狂与疏离反抗的孤寂。《威利》或许更能代表整部结集的古怪狂乱。它表面上是一个告密者的故事:男孩向父亲告发母亲的淫荡通奸,实则挖掘了儿童的破坏欲与性意识的转换游戏。威利报复母亲时的虐待欲望,完全源于对母亲的占有幻想。他想替代那个通奸者。厌恶与恶心都基于占有的失落。《家族的作家》与《世界博览会》让人想起风月宝鉴,一阴一阳,正照反照,情感结构却惊人相似。祖母与母亲的怨恨、母亲对父亲的抱怨、母亲对大姑姑的反感高度一致,相互贯通。即使将二者视为姊妹篇,也未尝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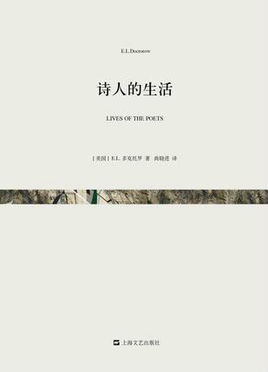
《诗人的生活》 (美)E.L.多克托罗 著 尚晓进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5年6月版
2
《世界博览会》并未像《家族的作家》一样,最后以一封反讽信宣泄不满,而是以参观博览会的一抹亮色维系了家庭温情。多克托罗是迷人的,他的文字里内置着温度计、晴雨表,叙事中悬挂着情绪线。很难想象,凡俗的家庭碎戏能写出什么新花样?是不是只有加些猛料:骇俗的不伦之恋、惊悚的罪案情节、悬疑的哥特气质、凌乱的情感纠缠才能满足读者的猎奇兴致?多克托罗没有那么LOW,他敢于面对凡俗的人生与无聊的本质,在无事里写出况味,在平静里见出微澜。他品味各种内在张力、静默冲突、巧妙制衡,从而找出家族氛围、宗教传统与时代语境的内在关联。小说中,家族对矛盾与疏离总是羞于承认,这是被遮蔽的密约。作家以爱的力量写尽痛苦的幽微,以力的解析道出矛盾所在,“从我母亲和父亲那里展开的是家庭的双翼,它们的力量不相等,因而使我们的飞行不稳定。”日常风暴也是爱的象征。
说人易,谈己难。叙事者是自传体小说处理的鸡肋,太真切不免泄露隐私,太美化不免矫情浮夸。“我”(埃德加)理解能力有限,缺少分析,观察却更近真实。而母亲、哥哥和姑妈的插述补叙让小说顿时成为多乐章的大型交响,它再次彰显了作家的音乐气质。在“我”看来,父亲的形象带着优越的自信,他是生活的引领者、文化的启蒙者、城市的主宰者。“那时我就可以向成人文明的混乱状态敞开我的思想,知道他会为我找到秩序。”母亲对父亲却含着不满与烦躁,她的抱怨是对“我”的逆向增补与拆解。多克托罗在此有意模拟了福克纳《喧哗与骚动》不同人讲一个故事的戏法。不过,作家有着自己的变奏和装饰音,他没有一味独白,而是以埃德加为潜在对象形成倾诉的对话。这使小说华丽而不失质感。
世界博览会成为作家的最终布景与秘密道具,伏笔长、出现晚,有如相声的抖包袱与解扣儿,展示着“明日世界”这一主题对人类生活的幸福允诺。而当“我”看到诺玛表演裸体章鱼舞时的不忍与疼痛,也反思了城市将人低俗景观化的倾向。诺玛与梅格的相伴教会“我”尊重女性,征文比赛让“我”铭记:犹太人的民族认同与美国男孩的成长其实是同一个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