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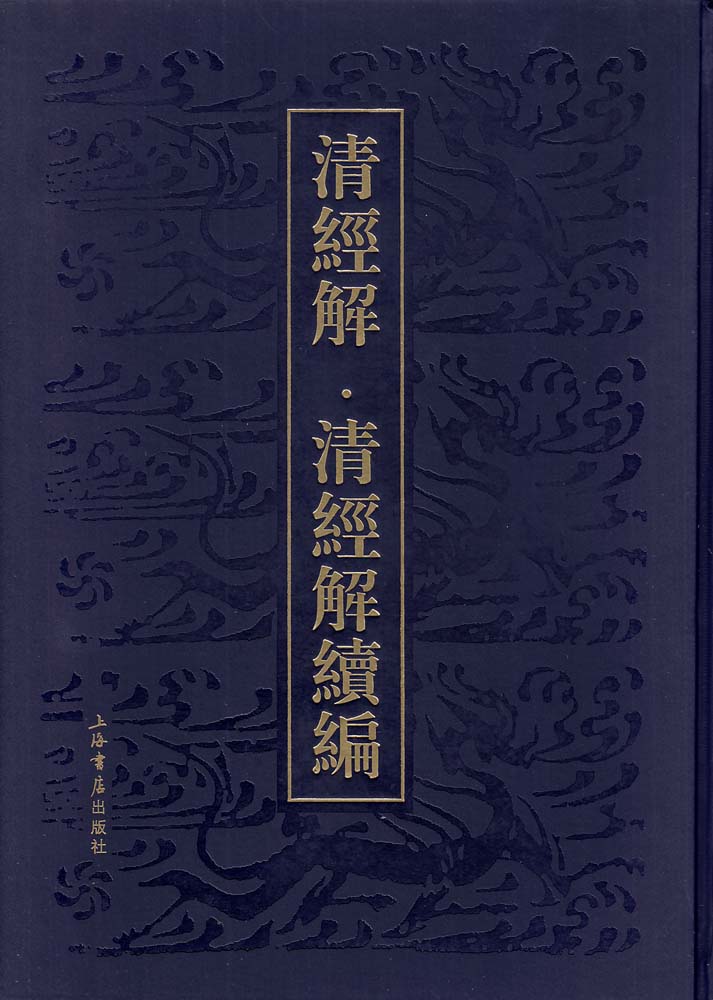 在家藏数万册书籍中,复本是难免的,但同一种书拥有五种版本的,只有《清经解》。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学丛书占位太多,却至今不愿转赠,是因为我与她们有一段难以忘怀的书缘。《清经解》是我学术生命的灵魂,而这五部书正是我学术经历和足迹的见证。 在家藏数万册书籍中,复本是难免的,但同一种书拥有五种版本的,只有《清经解》。这部卷帙浩繁的经学丛书占位太多,却至今不愿转赠,是因为我与她们有一段难以忘怀的书缘。《清经解》是我学术生命的灵魂,而这五部书正是我学术经历和足迹的见证。
20世纪70年代初,我带了一套石印熬《康熙字典》去苏北下乡。书荒的年代,无书可读,偶尔借到几册唐诗宋词,都整本地抄了。再要打发时间,只能拿《字典》来消遣。”文革“时才小学三年级的我,能识得几个字?勉强含糊翻看,不过是囫囵吞枣、依稀仿佛而已。至于书前《四声等韵图》中的黑白圆圈和见溪群疑等字母,更是不知所云,这就是驱使我后来自习音韵学的强大动力。1978年上调回城,被分配在自行车厂当流水工,干的是卓别林《摩登时代》的工作,早中两班轮番,业余时间就沉浸在上海图书馆钻研等韵学和古音学。因研习古音而走近经学,因经学而关注训诂文字,因传统小学而叩开乾嘉学术之门。当时上图参考阅览室对我厚爱有加,每天保留的书总有几十册,像《刘申叔遗书》《王静安遗书》和《崔东壁遗书》等都曾长期保留过。偶尔听人说,乾嘉学术著作之精华,大多被搜罗在大型丛书《清经解》中。抱着侥幸心理,去上海古籍书店碰运气,奢望一编在手,全部拥有,但也明知价格绝非我能承受,只是幻想而已。
那时书店不开架,看书要请营业员拿。时间一长,熟识的书友多倚靠着柜台与营业员闲聊。一天,在书店碰到一位买书友,谈起《清经解》,他神情自得地说,70年代初,他用四元钱买到一部石印本正续《清经解》(当时石印熬的市价是一毛钱一册,他显然便宜了一元多),里面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念孙《读书杂志》、王引之《经义述闻》等。我听着听着,觉得原来的幻想可以变成理想,只是书店目前没有存书。于是我与他攀谈,请教尊姓。他姓崔,与我交换了电话。我表示要是长期寻觅不得,是否可以惠借,或从中借几种,他表示可以。之后一段时间,我隔三岔五地去书店问,结果当然是失望而归。失望久了,曾忐忑不安地拨通过崔先生的电话,得到的当然是无须预料的结果。四元钱可以买一部,即使有所上涨,我也能够承受(农场回沪的工资是三十元六角,须半年后转正拿三十六元),于是四处拜托朋友,祈求能有私人转让。该是冥冥之中的吉人天相吧,我中学林姓同学的弟弟说,他南通的舅舅有一套愿意出让。亟问其价,索要五十元——我一个半月工资的数,十二倍于70年代初的价!我是一个书买不到买不起就会经常做梦的人,所以下意识觉得必须买下。思念一定,立刻去十六铺码头买船票。哪知船票告罄,路边的黄牛要我三倍的价——三元六毛,我毅然买下。那是晚上十点我去农场的一班轮船。我提着一只那年代都是自己买料做的黑色旅行袋,揣着念想,在昏黄的灯光下半梦半醒地度过了六七个小时。凌晨五点到南通,边问边摸,到了同学亲戚家。渴望他给我先看书。他说书在单位,要下班带回来,让我先睡。怀着无奈,挨着日头,等他把书带回来,已是上灯的时候。我匆匆点了数,点石斋石印本《清经解》二十四册,鸿宝斋石印熬《续编》三十二册,付了钱,旋即踏上回程的船。船舱内,我忍不住拉开旅行袋,取出字如蚊蝇大小的石印本,在暗淡的灯光下阅读观摩,竟发现《续编》最后两册是配本,一丝遗憾闪现,旋即又被实获至宝的欣喜淹没。那年代提着旅行袋挤在船上蜷缩的,不少是投机倒把做小生意的人,我不在意人家怎么看我,而我似乎既被投机倒把了一回,又想趁此投机倒把一回,用沉重的代价换得了日思夜想、久觅不得的书。这种付出的心痛和得到的欣喜,让我产生错觉:有了这部书,就拥有了这部书的知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