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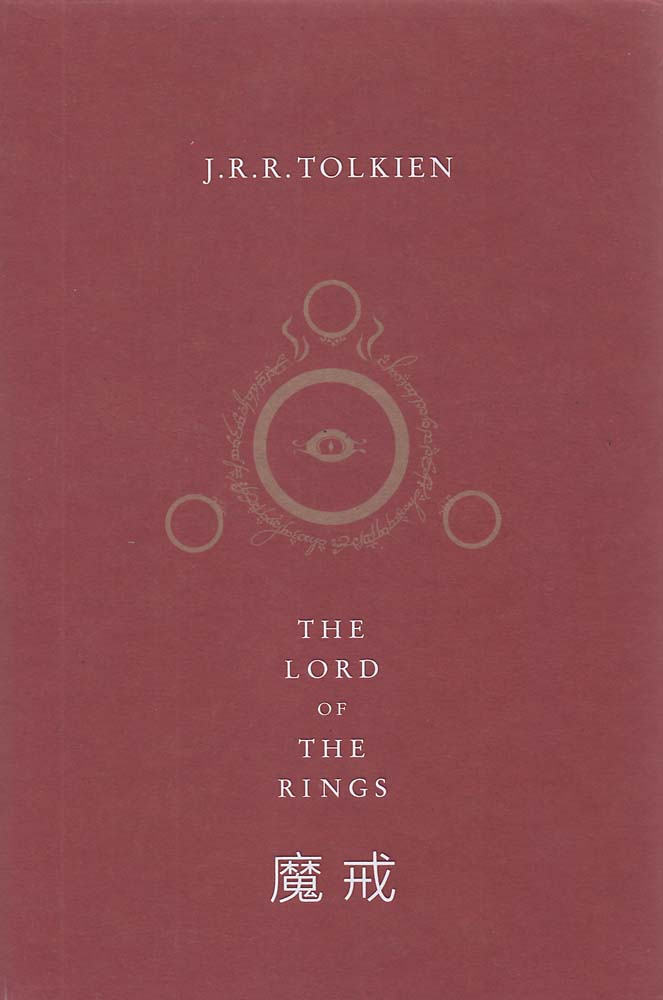 如果说彼得·杰克逊打开了托尔金魔戒世界的华丽大戏,把这个名叫“中洲”的奇幻世界向世界展示出来,那么为这个奇幻大舞台支起精美绝伦帷幕的必定是艾伦·李(Alan Lee)和约翰·豪(John Howe)两位世界级的绘画大师。没有两位大师多年绘制《魔戒》插画的积淀,很难想象彼得如何塑造电影里那个庄严而又奇异的庞大世界。 如果说彼得·杰克逊打开了托尔金魔戒世界的华丽大戏,把这个名叫“中洲”的奇幻世界向世界展示出来,那么为这个奇幻大舞台支起精美绝伦帷幕的必定是艾伦·李(Alan Lee)和约翰·豪(John Howe)两位世界级的绘画大师。没有两位大师多年绘制《魔戒》插画的积淀,很难想象彼得如何塑造电影里那个庄严而又奇异的庞大世界。
比起约翰·豪华丽又略带夸张的绘画风格,艾伦·李的画风更倾向于朴素飘渺的质感。正像他喜欢的素描和水彩介质所表达的,留白和素色为画面笼罩上一层淡淡的薄雾,偶尔从间隙里透出细密扭曲的树枝,以及人物略带诧异或者严肃的眼神,让人产生越发想看透这画面后的世界的欲望。
几乎不用艳丽色彩,平添了几分史诗感
艾伦·李使用很少的颜色。在大部分绘画作品中,他谨慎地使用着蓝色绿色和少量的黄色,几乎不用红色和象征着魔幻的艳丽色彩,吝啬的用色不但没有使得画面单调反而平添几分旧时绘画的史诗感,和《魔戒》故事氛围契合。
正如托尔金写作《魔戒》的时候,整个欧美的奇幻世界还仅仅局限在各国的传统神话故事以及多种宗教故事中,《魔戒》从中汲取奇幻和思想的养分,糅合了那个时代的社会人文以及托尔金人生的磨砺,更添加了他对人生的渴望和寄托。
这个世界如同《精灵宝钻》中伊鲁维塔创世时候的乐章宏大而又丰富,每个试图了解这个世界的人都只能瞥见一部分。因此艾伦 ·李如同站在这迷雾的大海边,努力看透这个世界,而迷雾将中洲世界大部分色彩褪去,留下那些欲盖弥彰的轮廓和模糊的影响。如同艾伦·李草图式的风格,让我们留下更多的想象空间。
“素而不简、繁而不杂”
虽然没有太多色彩,艾伦·李用他坚实的素描和构图技巧充实了画面。每次看他的画都会惊叹于他对植物尤其是树枝那种执着的细致描绘,仿佛活生生地蜿蜒生长着,努力纵横交错,一幅画面中可能会有几种树,通过他的画笔这些树组成了一片丛林,又似乎是编织起一片精美的绣品。
在自然蔓延的树木衬托下,艾伦的建筑坚挺依然,无论是深色背景中留白的米那斯蒂利斯城,还是无法摧毁的黑色奥桑克巨塔,抑或是夏尔乡村那贴近丘陵的霍比特人袋地洞,都用或挺拔或圆润的线条将这些造物凸显出来,从中我们知道了托尔金用哥特描绘邪恶,用古希腊代表文明,而他最爱的英国乡村则代表了希望和归宿。
有着美丽繁复背景的承托,艾伦·李笔下的人物越发显得朴素起来,不论是如同隐士简朴的甘道夫,乡绅打扮的巴金斯,还是满身戎装的刚多骑士,即使是书中文字无法言喻之美的精灵女王,也不过一身长袍,体现了艾伦·李“素而不简、繁而不杂”的风格理念。
有时候细观艾伦·李的人物,人类精灵并无美艳英俊的样貌,巫妖兽人也是似人非人并无出奇之处,但是结合朴素颜色和有张力的线条,这样的样子反而与水彩和素描的简约大概的感觉一样契合,并无突兀之感,反而体现一片和谐,平衡掌握得恰到好处,画面上的每个元素都彼此保持着节制,唯独人物那些或专注或紧张或平和的自然表情点缀其间,为画面平添亮点。
少用色彩,而注重线条,对线条的专注引出他对纹饰和图案的专注,看了描写魔戒电影拍摄过程的纪录片,其中很多时候看到艾伦在低头描绘图案,有服饰上的,又有建筑梁柱,乃至瓶罐饰物上的细枝末节都来自一笔一画的描绘,由此可见细腻是艾伦作品的特点,为此不论是树枝还是裙摆的皱褶,都会花大力气描绘,但这只能涵盖艾伦艺术特色的很小的内容。
就像在原野里肆意狂欢后,喝上一口热茶收敛心神
真正吸引我的还是他对画面整体气氛的把握,有时候觉得就像在看一幅中国水墨画,浓墨淡彩,利用水彩颜料的特性和水彩纸的肌理,在画面上铺呈出多变的山川、树木、建筑、人物。颇有中国画大写意山水和细致的工笔技法结合的微妙,这也是我觉得他与其他魔戒画家乃至奇幻艺术家最大的区别,不知道艾伦有没有接触过东方艺术和中国古典绘画,如果有,他很好地体会到了艺术的精髓,而他擅长的水彩也正是融合东西方绘画的最好介质。
艾伦与豪的合作始于《魔戒》,直到在新西兰飞机上与剧组一同前往实景踏勘之前,两者还都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状态,两者保持着相对独立的创作风格,彼此创造着自己的中洲世界。
有时候觉得豪的作品大气磅礴,动感十足,第一眼肯定很吸引人,也难怪彼得·杰克逊的电影很多场景设计都来自豪的作品设定,的确吸引了观众。但是反观艾伦的作品,虽然与电影处在若即若离的状态,却与原著的氛围如出一辙,有空时候我一边翻阅《魔戒》的小说,一边配合艾伦淡彩和素描般的作品,体会到两者之间有那么点微妙的联系,好像托尔金大师亲自在一边描摹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