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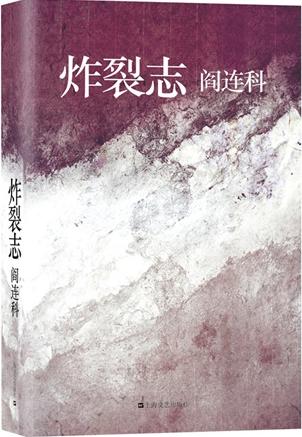 先讲一个故事…… 先讲一个故事……
如果你来找我,站在我面前,信任我,你问我:给我推荐一本书吧!
好。我也知道你的习性,你喜欢外国小说,内心幽暗,生活低微。你需要一本新书,我扒开书堆,翻出今年刚刚译到中国的“文痞”布考斯基的小说《苦水音乐》,拿给你。
就是这本了,它适合你。
你也相信我。你回去的路上给我发来短信:嘿,哥们,这小说,真好看!
事实就是如此。
就在前几天,我的一位朋友,编得一手好书,来打听今年的凤凰网年度好书。我秘而不宣。他说,王先生的书,上半年好评如潮,下半年他们却一边倒地留下几句批评,没了!
他很生气,我也理解。媒体的好书榜年年有,开书单的却总是那几位老面孔,何况媒体的朋友们有时还没有耐性,像根怕疼的触角,碰到一点,便退缩了。
可那边瑞典文学院,也是那几把旧椅子。有什么办法?
好书那么多,我只选十本。
现在开始闲话正题。
“凤凰好书榜”自2008年开始评选“年度好书”。当年,我们推荐九本书,网上可以查到,其中有爱伦堡的名作《人·岁月·生活》,一本叫做《长路漫漫——一个童兵的自述》的战争小说。现在看来,那是一份蛮片面的榜单。
2008年,我们没有推荐鹿桥的《未央歌》、君特·格拉斯的《剥洋葱》、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沈昌文的《知道》。
转述当年一位读书人的话讲,“由南方一家报业选出的年度十大好书出台了,仔细看一眼书单,除了几本附庸风雅的随笔,余下的皆是政论财经之类的读物,竟然没有一本诗集和小说,感觉是老干局推荐给街道办的社会资料。殊觉怪异。据说,这些书是记者和学者推荐的……”
一位读书细致、较真的读者,他拒绝接受一份“不合我意”的书单。好比一张肉食菜单之于素食者,好看而无用。
书单有没有用?依我的个人经验,是有用的。它不一定是一份正式的“书单”,每本书前面标好“一二三四……”,等着你与它相遇,接受它的奉赠。
叭如追溯我的读书史,直接的起点是余某人的自传性书信体爱情小说《香草山》。这位世纪之交以《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风行中国校园的北大怪才,有一份近乎完美、令读书人垂涎的爱情。《香草山》不仅极尽碑情之浪漫,更以他和他那情投意合的爱人的博学,鸿来雁往间提供了一份不小的书单。
记得它的开篇引有当年红到妓女荷包的余秋雨的散文所引罗素的话。它提到《沉沦的圣殿——中国20世纪70年代地下诗歌遗照》,为我打开一份灰色年代的秘密书单。那个时代,那些人,那些书和文,军队一般冲进我的身体,成为我实际意义上的阅读启蒙。
就是这般。读者和书,仿佛恋爱的双方,未相爱前互相寻找甚至互相等待。读者等一本好书,一本好书等它的读者:他/它们各自将心愿写在书单上,等着相遇。也像恋爱的双方,读者和书必须是合适的,缺了一方的欢喜,都不行。
书单有很多种,新华书店的书单,万圣书园的书单,张老师的书单,作家王二的书单,好书单,烂书单,历史书单,文学书单……我们出好书单:“凤凰好书榜”。
所谓“好书”,需要界定,读者不明白,开书单者是要清楚的。以凤凰网读书频道对好书的评价标准:所谓好书,一要读得舒服,文章要好;二要读来有所收获,言之有物。用写在我们页头上的话说:文字之美,精神之渊。
多年下来,我们有自己的偏爱,也有偏爱我们的读者。我们只通文学、文化、历史、政治、生活,抱有人文情怀,偏好思想之书,不对类型小说、童书、教科书等说三道四。
有了标准,来看开书单之人。这里头也有讲究。比如梁先生读书很多,却不爱给人开书单;李先生读书精深,半辈子只向人推荐两本书。只有书店老板、先生教授和书评人等十分辛苦,日复一日地读,读不好书,不敢提荐书的事。
我们所邀请的年度好书评委,二十一位开书单的人,包括大学教授、研究所专家、作家、书评人、读书媒体人、书店老板、出版家。他们是:
氨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晓明;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何怀宏;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杨念群;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
《中国图书评论》执行主编、南开大学教授周志强;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陈众议;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勇;
学者杨早;
作家刀尔登;
《世界文学》主编余中先;
《读书》杂志执行主编郑勇;
上海书评主编张明扬;
新京报书评周刊主编萧三郎;
资深媒体人胡洪侠;
氨京万圣书园创办人刘苏里;
立人图书馆总干事李英强;
知名出版人俞晓群;
书评人止庵;
凤凰网读书频道主编严彬;
凤凰网读书频道图书责编何可人;
凤凰网读书频道”读药周刊“责编陈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