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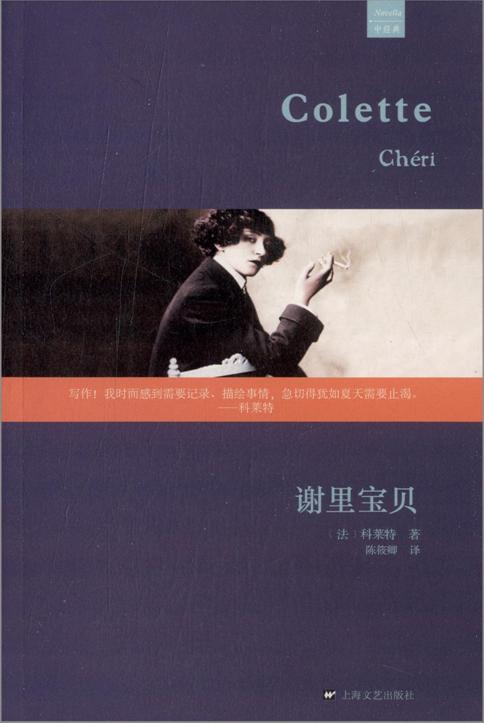 谢里是谁?他首先是个棕红头发的小家伙,一只肩膀稍微有点斜,粉红色的睫毛,右眼视力弱,患有慢性鼻炎。他一脸穷孩子的样儿,但却有一百五十万法郎的零花钱。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在巴黎等待着黎明的曙光照到泛着蓝色的凄楚的窗子时的每一处地方,他都涉足过,跟在一个揭发、严厉但却很光鲜的玩弄他的情妇身后,像条尾巴似的。我要补充一句,谢里那时候还叫克鲁克,因为他每一喘息,感冒似的鼻子里就会发出轻微的让人受不了的声响,像活门的开关声。我想他鼻子里大概是长有息肉…… 谢里是谁?他首先是个棕红头发的小家伙,一只肩膀稍微有点斜,粉红色的睫毛,右眼视力弱,患有慢性鼻炎。他一脸穷孩子的样儿,但却有一百五十万法郎的零花钱。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在巴黎等待着黎明的曙光照到泛着蓝色的凄楚的窗子时的每一处地方,他都涉足过,跟在一个揭发、严厉但却很光鲜的玩弄他的情妇身后,像条尾巴似的。我要补充一句,谢里那时候还叫克鲁克,因为他每一喘息,感冒似的鼻子里就会发出轻微的让人受不了的声响,像活门的开关声。我想他鼻子里大概是长有息肉……
有一天,我在《晨报》上要撰写我每周的故事时非常地需要他,因此谢里第一个屈辱的形象便诞生了。他承认自己胆小怕事,而且对孤独害怕得要命,他忍受着自己情妇的坏脾气,而他的朋友们则又敲他的竹杠。
但是,有一天,他在与他那黑发闪亮、模样凶狠、要求强烈、目露凶光、浑身珠光宝气的女伴单独进晚餐时,他瞥见邻桌有四位成熟的女士。桌上没有男人,只见她们四位在喝半干香槟酒,吃螯虾、鹅肝、甜点,欢声笑语,大谈各自的过去。克鲁克影影绰绰地看见了自己的命运,也就是为了被爱而重生再去死的命运,也就是要英俊美貌。
克鲁克像是被我灌了南方的一种烈性麻醉药似的,怯懦地失去了知觉,沉人深渊之中,醒来时却倒在蕾雅的怀里,后者便称呼他为“谢里宝贝”!
于是,我立即为谢里量身定做一个美好的外表:二十五岁。褐发,皮肤白净,像一只六个月大的雄猫似的鲜亮。有时候,我退后一点好定睛看他。我在不厌其烦地美化他。漂亮的眼睫毛,如乌鸫羽毛似的秀发,双手纤细,胸脯硬挺,状如盾牌,还有那副牙齿!嘴唇如弯弓……我不知道如何才能让他尽善尽美,于是便送了他这么一件高贵的礼物:威严,有荣誉感,还有那些大的拉皮条者的那种幼稚气。对于一个游手好闲和收入颇丰的小伙子来说,没有什么比这更加使人精神振奋的了。谢里舒心惬意地叹息着,伸伸懒腰,然后便跑到他觉得高兴的地方去。
在二十岁左右的那一代人(而我则是四十岁左右的人)中,他爱找那些其父是浪子的那些放荡不羁但却谨慎行事的年轻人。这些怪诞的孩子不加考虑地花钱如流水,但是像是飞去来器似的,钱又巧妙地回到他们的手中。一辆昂贵的汽车,几匹骏马,一艘游艇,一件无与伦比的裘皮大衣,稀罕的珍珠,他们全都在享用。争强好胜的秉性在激发他们相互攀比,争着扮演坏孩子、小混蛋。这些误人歧途的孩子中有一个还故意容忍他的女伴在马克西姆餐厅用餐时夺走了他戴在手上的一枚漂亮至极的戒指。但是,第二天夜晚,他像一个优秀的杂技演员似的,凭借着墙上的铸铁器件,便爬进窗户敞开着睡觉的那个年轻女子的房间里去。他打她,夺回了戒指,而且,考虑到自己的名誉起见,还偷走了她的一条项链。年轻女子在讲述此事时,不乏赞美崇敬之情。
从恶中产生良药,或者产生另一种人们认为是有益的恶来。瓢虫治住了圣约瑟的虱子。在朝向急躁无耐心的年轻女子无法达到的终点奔跑时,那些胸有成竹的女冠军们冲上前去了。她们在运用自己的那些令初出茅庐的年轻偷猎者目瞪口呆的办法。如果不在这些重量级的女骑士那儿去找,我又能去哪儿寻找到我的。坏婴儿”呢?有时是金发,有时是褐发,往往很富有。有时却又很贫穷,他似乎生来就是为了让我惊愕茫然的,而我又真的会茫然无着的,如果我以前没有因《克罗蒂娜》而获知一种文学创作是可以拥有一部分怪癖的话。
我不习惯担心幽灵显形的魔法,所以作为开始,我笑对谢里,我向他伸出手去,我那手上赞扬他的墨汁尚未挥发干。在他开始一连串的肆虐之前,如同一种颇不懂人情世故的时尚所希望的那样,他出现在我眼前,是在某个女人那儿,这种女人颇有教养,有洞察力,但并非十全十美,时机成熟时,她们会毫不费力地便把一颗忘恩负义的、带刺儿的年轻的心灵捉拿到手。
我第一次认认真真地瞧着谢里时,他坐在一张天蓝色锦缎长沙发的边上,在逗夫人的小爱犬。他的睫毛的阴影在他那二十二岁的年轻人的面颊上晃动。脸热辣辣的,一直红到耳根,好像它属于太阳自他童年时起就在沐浴它似的那种鲜嫩的肉。他来自外省的一个贵族家庭,想到巴黎谋个前程。他确实谋到了这份前程,但是那却是另一码事……他女友的威严、声音的坚定、脾气的始终一致使她完全像是那个控制着谢里的女人,我在她的脸上读出了那份专断独占的爱,那是一种事事提防的幸福的猜疑,是半老徐娘内心燃起的那种亲密。
“把米奇带到花园里去,天气很好。”她冲着英俊迷人的年轻男子说。
我认为伊尔玛,或者伊达,或者蕾雅想向我展示谢里在狭小憋闷的花园中转着圈跑的样子,如同马贩子在拉着拴马绳让马奔跑一样。我还认为她是想与我单独待一会儿。
但是,目光跟着同狗嬉戏的男孩转动的金发女士既有点恬不知耻又有点矜持清高,而且对于自己作为泼辣专断的情妇的争执以及出钱买欢笑的成功经历也只是一笔带过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