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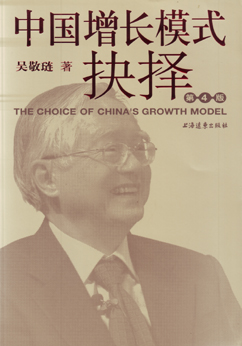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是制定“十一五”(2006-2010)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它详细地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相关问题。这本书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但是,在那次大辩论看似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中国增长模式抉择》这本书,是制定“十一五”(2006-2010)规划前的一场大辩论的产物。它详细地讨论了诸如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如何通过改革建立实现这一转型所需的制度环境等相关问题。这本书从初版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八年时间。但是,在那次大辩论看似已经取得共识的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增长到集约型增长转型的问题,至今仍然困扰着中国。
在中国的理论和政策讨论中常常发生一种“引喻失义、数典忘祖”的现象。一种观点或政策经过辩论好不容易被学界和政府官员普遍接受,写进了党的文件,成为政府的工作指南,可是不要多久,在人们头脑中保留的,往往只是一句空洞的口号,至于它的内容,则在实际执行中发生飘移畸变,甚至完全走样。
经济增长模式转型问题,就是一个相当典型的例子。
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发展”到“集约发展”的转型,是“九五”(1996-2000)计划明确提出的要求。然而经过了三个多五年计划(规划),这个要求并没有得到实现。由此导致粗放发展引起的种种恶果,例如资源枯竭、环境破坏、投资过度、消费不足、货币超发等等问题愈演愈烈。“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或“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究竟要从哪里转向哪里,也往往成了问题。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政策摇摆,方向不明。
凡此种种,都表明重温世纪初那次大讨论很有必要。重印这本书也有一定的价值。
1.本书的写作背景
这本书的第一版是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在2005年11月出版的(版权标注为2006年1月)。在此之前,为总结“十五”(2001-2005)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经验,研究如何制订“十一五”(2006-2010)规划,针对应当按照什么样的工业化路线和增长模式规划中国的国民经济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讨论。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苏联经济学家和党政领导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提出的一条重要的经济工作方针。
苏联在建国初期采取了发达国家在十九世纪通行的经济增长模式,靠大规模投资于重化工业推动国家工业化。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要求迅速发展重化工业,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他认为,为了同西方国家相抗衡,苏联应当尽快建立自己的军事工业基础。这本来是在当时情况下采取的一种政策安排,但是斯大林为了在党内斗争中给主张平衡发展的党内竞争对手布哈林戴上“反党、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就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提到“社会主义工业化路线”的高度,并且杜撰出“积累(即投资)是扩大再生产(即增长)的唯一源泉”的“马克思主义再生产理论的基本原理”。
从此,采取西方国家早期增长模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就成为遵循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唯一可能的选择。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苏联人却发现,采取这样的增长模式,由于抑制了要素使用效率提高这一增长的另一源泉,苏联在赶超西方国家的征途上遇到了不可逾越的障碍。于是,他们提出了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必要性。苏联经济学家采用与现代经济学生产函数分析相类似的方法,把主要依靠增加生产要素投入实现的增长叫做“粗放型增长”,而把主要依靠要素使用效率的提高实现的增长称为“集约型增长”。苏联党政领导接受了经济学家的分析,在往后的每一个五年计划中都提出了从前者向后者转型的要求。虽然由于未打破苏式社会主义体制和意识形态的障碍,转型并未取得成功,但是他们无疑提出了一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重要问题。
在当时,苏联的讨论并没有在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只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到选择正确的经济增长模式无比重要的意义,并且在1995年正式把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到集约型的转变”规定为“九五”(1996-2000)计划的一项基本要求。
“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型,由于是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后的改革大推进同步进行的,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十五”(2001-2005)在“九五”取得的成绩面前,却对经济增长模式转型有所放松。“十五”计划提出的新口号,是“坚持把发展作为主题”,“把结构调整作为主线”,要求“把调整产业结构与调整所有制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结合起来。坚持在发展中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在经济结构调整中保持快速发展”。
在“九五”取得的成就的基础上,我国的城市化开始在二十一世纪初期迎来了一次新高潮。在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下,城市化使政府手中掌握了价值以数十万亿元计的资源。于是,开始了大规模投资建设“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的运动。在理论和政策层面上,则表现为所谓“中国已经进入工业化后期的重化工业化阶段”学说的兴起。许多地方卷入了“造城运动”和“重化工业化”的热潮,在政府的主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大规模的重化工业投资和新城建设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