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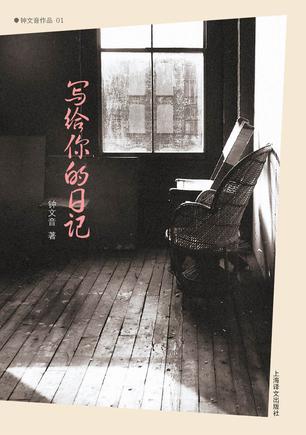 台北——纽约 台北——纽约
时差:十二个小时
飞行时间:十七个钟头
机长报告:还醒着的旅客可以看看窗外,伟大的纽约夜景,也请旅客系好安全带,空服员请就位,准备降落了。
纽约繁华瞬间就在眼前,华丽的黑丝绒上点点光辉在风中摇曳。从机窗看到疲倦的脸庞映到了透明玻璃上,当下突然明白这一举步,似乎看到了往后将不断长途跋涉的自己。
那一年,站在十字路口张皇过久,心情的版图只是蜘蛛匍匐于网中的距离。岁月的湿气浸淫到生命的骨子里,蔓延成一种虚妄的不安。
出走,也可以是一种存在的静止方式。
某月某日,突然机缘之手似那午后的一声雷鸣,轰轰然来到眼前,将自己逐出沉溺不堪的记忆,载我毅然飞向陌生的纽约大城。
纽约,寂寞城市。在这样的虚张声势里,幽幽怀想起出国前的雨夜,二十四小时的豆浆店,热炸油条的哔啵响。风雨把沿街游荡的流浪犬给驱到了骑楼,包括我这个游荡的小兽。
躲进二十四小时便利店,翻阅着八卦杂志,茶叶香气和湿气黏和在一起,让每个离家的旅人,片刻里织补了破碎的心。
到纽约前,我不过是个破碎的人。所谓的破碎就是,自身找不到和自身依偎的重量,遍寻不着情爱的实质风貌。在数字年月里排遣青春,时间以巨大的轮轴把我碾了过去,一回又一回。
直到我动了身.时间之河才冲破了阻塞,我听到了指针在河面上愉悦地跳跃着。
长久让身和魂安居一地,于我简直是,除非上帝特别垂爱,否则安不了心。即便身不移,魂却早已思迁。
因为出生的时辰定数和个性使然,因为早早看清了情爱的不灭与幻灭本质。
有些事情从来没有过去,有些角落却总是让人遗忘;有些气味挥之不去,有些人在心口生了根;有些旅地仿佛前世已走过,好比纽约,好比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的皇宫……
常常,突然而来,突然而走。
没有预警的生活哀乐和放逐者无边无际的寂寞况昧,嬉游者的喃喃自语和两地牵盼,我在纽约街头的咖啡馆,写下了如此这般的单身旅人手记:以日月为经纬,以无常为主轴,以寂寞为调味,以相思为节气,以自语为形式,以惘然为结束。
真实的日记本,充斥着当下手写的糟乱与随性的涂鸦,饱满的生活物件,在这本书里遁去,那样原始的混乱和涂写毕竟是不合于常态的出版。换句话说,虽以日记名之,但记录书写的角落大抵是光影可以照射之处,没有阴暗至必须掩卷喘息的内容。
若有阴暗,也不过是浅浅流动的感叹和虚妄,也是纽约这个城市当时的自我反射。
这是一本有条件筛选下的日记文本。当你打开它时,你就准备进入了一个单身旅人的生活声色;我相信你也是个旅人,我们在人世里本身就是个旅人,于是就让我们“一个旅人望向一个旅人”吧;至于城市的本身,纽约已经有太多人书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