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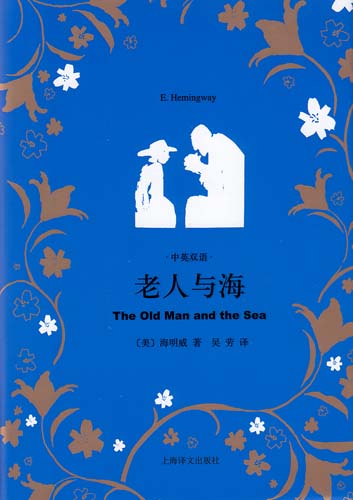 前阵看莫言的一篇文章,读到他“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一个擅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路”之类的论述,复又联想到十几年前,王朔写完《看上去很美》质疑前辈作家“没写过长篇小说算什么小说家”(大意好像如此)的言论,不禁有些感喟:当代小说家对小说文体的思考,没有因市场化和电子阅读的冲击而停滞下来,这对今天貌似渐离盛景的汉语小说,实在是希望之所在。但怎么样思索,才更贴近现代的理性,并能惠及一个时代的创作,恐怕还是需要不止一两代作者和研究者的心血的。 前阵看莫言的一篇文章,读到他“长篇就是要往长里写”、“一个擅写长篇小说的作家,不一定非要走短——中——长的道路,尽管许多作家包括我自己走的都是这样的路”之类的论述,复又联想到十几年前,王朔写完《看上去很美》质疑前辈作家“没写过长篇小说算什么小说家”(大意好像如此)的言论,不禁有些感喟:当代小说家对小说文体的思考,没有因市场化和电子阅读的冲击而停滞下来,这对今天貌似渐离盛景的汉语小说,实在是希望之所在。但怎么样思索,才更贴近现代的理性,并能惠及一个时代的创作,恐怕还是需要不止一两代作者和研究者的心血的。
小说因为什么在今天得以继续活着
每一种历史悠久的艺术,在面向当代和未来的展望时,都会思考到存在的必要性。小说当然也无例外。记载生活、塑造形象,帮助读者在无害、低成本的前提下消费情感和时光……这些自小说这一文体诞生起,便被视为其体裁特色与长项的因素,伴随着几百年来社会分工的裂变、人类生存处境的多样化,以及社会人文思潮的繁复,都变得不再那么确认无误了。比如那些著名如“小说家是时代的书记员”之类的论断,随着文本的丰富,和“多元化”与“宽容”深入人心,都不再构成唯一的律条。
那么,构成小说今天独特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呢?墨西哥文豪富恩特斯引用过的一个奥地利作家赫曼·布罗奇的提问,或许可以构成对中文作家们的一个启发:“哪些东西是只能通过小说而不可以通过别的任何方式来表达的呢?”当然不再是“讲故事”了(虽然“小说就是要讲故事”这种观点三十年来甚嚣尘上)——评书、曲艺、戏曲、电影、电视剧乃至纪录片都可以讲故事;当然也不仅仅是回忆一次爱情、再现一场战役或一个人、一代人的一生。
“小说不仅反映现实,而且创造出一种新的现实,这些事实原本不存在,可是现在如果没有它们,我们甚至不能体会到真正的现实了。”“小说赢得了批判世界的权利,那么它首先就要展示自我批判的能力。”我坚决同意富恩特斯的这种阐释,因为这种对小说与现实关系的理解,可以矫正过去一百年来,同胞把“现实主义”降解为“写实”、“拟写实”乃至形形色色服务、宣泄的“工具论”的做法。所有的小说当然都是指向现实的(从这种理解上,我们可以说作为文学史和美学概念的“现实主义”名字起得有点狭隘了),哪怕作者志在逃离,哪怕它们是通过魔幻和变形、自我诋毁的手法去抵达现实。
而在确认以上这些后,我们稍许专业性地讨论一下小说在今天的不同长度的存活理由。
长篇小说——复调的种类与浓度
一部长篇小说能否得以流传,不在于它的字数而在于它的质量,这是读者与作者公认的看法。仅仅写一个人、一场爱情、一场社会剧变的小说,曾经有过可以成为名著的可能——但那是在过去。事实上,伴随着文学作品的叠加,阅读和购买群体的分化,严肃写作在向别的领域和文体贡献出一部分“讲故事”功能之后,它所承担的取样人类精神和心理的任务大大增加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同是主写刻骨爱情,伊夫琳·沃的《旧地重游》会令人掩卷长思,西格尔的《爱情故事》或沃勒的《廊桥遗梦》却只是畅销性的读物而已——哪怕它们曾令普通读者感动至深。
过往和今日高品质长篇在未来的长久流传,我认为相当一部分取决于它是否拥有“复调性”和“浓度”。
“复调性”可以表现在结构上,如《万有引力之虹》(品钦)、《法国中尉的女人》(福尔斯)、《米格尔大街》(奈保尔);也可以表现在小说所涉及的人类精神或时代,如《洛莉塔》(纳博科夫)、《小世界》(洛奇)、《耻》(库切)。而“浓度”则包含了小说的语言、情感、想象力与洞察力等指标。“复调性”和“浓度”兼具的,便可视之为杰作——如《白色旅馆》(托马斯)、《10又1/2人类历史》(巴恩斯)和《周末》(施林克)。
“复调性”和“浓度”比小说的厚度、故事奇异性,更能决定文本在时间长河的命运。一个明显的例子——同为诺奖得主作品,《我弥留之际》(福克纳)远比《我的名字叫红》(帕慕克)更具备上述指标的推敲性。而“中外小说史上已经存在过的杰作类型,是不是还应该由后人继续以描红的方式写出?”这是一个简单却富有挑衅性的话题,它将决定着长篇小说作者的野心。
短篇小说——文字的质地与目的地
短篇小说与“故事”的距离比长篇稍近。从起源上讲,它最初的目的,就是向读者提供“故事”。有时虽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但描写的也是一个具有独立蕴涵的时段中发生的事。早先的短篇小说名家,可以是一个优秀的段子或场景讲述人(比如欧·亨利、早期的契诃夫),但后来所提供的故事或场景呈现,渐渐变得具有“隐喻”、“回味”和“人生取样”的属性。作家在说故事人的表象之外,更多了些研究者的深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