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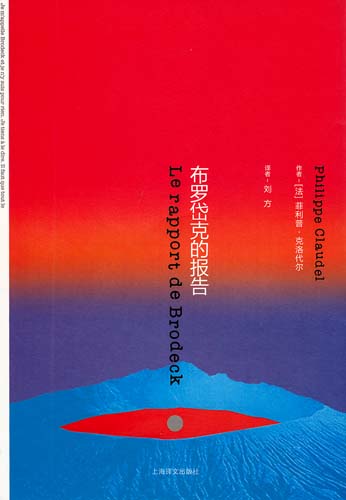 《布罗岱克的报告》并非是一个激发眼球效应的书名,它的作者菲利普·克洛代尔也是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一位法国作家,可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这部小说,却敢于挑战当下的阅读方式。 《布罗岱克的报告》并非是一个激发眼球效应的书名,它的作者菲利普·克洛代尔也是中国读者相对陌生的一位法国作家,可是,上海译文出版社引进的这部小说,却敢于挑战当下的阅读方式。
如今“快餐时代”的阅读,开端就惯常先将悬念乔装打扮一番,使它以具有足以撩拨感官欲望的容貌登场,以挑逗人们的阅读快感。可《布罗岱克的报告》却拒绝装扮悬念,仅凭借意识流的节奏,慢条斯理,将悬念用干巴巴的文辞——“另外那个人”和“发生过的事”作为指代——尽管那个悬念本身就具有谋杀、残害那股强烈的血腥气。
破译意识流的旋律,《布罗岱克的报告》的情节很清晰:二战硝烟初消的年月,在欧洲某一山区小镇,镇里的“文化人”布罗岱克奉镇长奥施威尔之命写份报告。报告内容是叙述“发生过的事”——那天晚上,镇里的男人们在客栈里杀死了“另外那个人”。布罗岱克并没有参与杀戮,却必须说明“另外那个人”来到小镇后发生的事,解释为什么镇里的男人们只能杀掉“另外那个人”。镇里男人们要求布罗岱克必须将报告写得让看到报告的其他人能“理解”、“原谅”这次血腥的集体谋杀。
布罗岱克压根不想写,可又不敢不写。他的邻居、退职官员戈布勒威胁他“小心点”;镇长奥施威尔将他带到猪圈,指着那些贪吃的猪群说:“它们可能吃掉它们的亲兄弟,它们身后不留任何东西,任何痕迹,任何证据,它们不知道什么叫悔恨,不知道什么是过去,它们活着,你不认为还是它们有道理吗?”镇长还警告布罗岱克说,你可以将自己的亲人——精神失常的妻子、幼小的女儿“当作不存在”。这警告可非同寻常,因为当纳粹铁蹄蹂躏这个山区小镇时,正是小镇里的男人们将两名并非当地土生土长的居民——其中之一就是布罗岱克,出卖给德军送入集中营,以此换得驻镇德军与小镇居民的平安相处;留在小镇的布罗岱克妻子的精神失常,也是遭德军轮奸所致。读这部小说的人们,由此就进入布罗岱克被押解往集中营后,惨遭折磨的痛苦回忆中。数个被纳粹法西斯精神毒化的人物,相继影影绰绰地现身,而且似乎始终存在于侥幸存活、返还小镇的布罗岱克的劫后余生中……例如:那个有“吞噬生灵的女人”绰号的集中营营长妻子。她是个金发白肤的美妇人,却抱着个孩子,来主持每天早晨吊死一名集中营囚徒的死刑。她在从容欣赏死者的痛苦状态后,还微笑着给怀中的孩子一个吻。可如此蘸美貌油彩,画丑恶灵魂之场景,在这部小说中,居然只是充当主体叙事的背景色彩。
一般说来,对于二战时期德国纳粹惨无人道罪行的控诉,往往是涉及那个年代的文学作品无法回避的时代场景,也多半是作品浓墨重彩之所在。西方文艺中描摹无辜民众在纳粹集中营惨遭折磨之痛苦的名作,可以说数不胜数。然而,《布罗岱克的报告》却将小说主人公在集中营遭受折磨的痛苦经历,仅仅作为铺垫、映照。作者着力叙述的,却是那“另外那个人”和“发生过的事”,以及那场谋杀;作者着力刻画的,竟是那凶案发生前后的血腥气之弥散和掩盖,以及掩盖得合情合理。由此可见,《布罗岱克的报告》立意之深:世人所公认的集中营折磨之大痛,在菲利普·克洛代尔的笔下仅作底色,可见作者全力展露的,必然是剧痛。
“另外那个人”是一位来小镇采风的外地画家,可他究竟做了什么必遭杀害?在此赘言,有可能会削弱人们阅读《布罗岱克的报告》的兴致。倘若说可以透露些许关节,那就来看看这个小镇的神父派佩。宗教职责使他可以通过“告解”仪式,听取小镇居民的忏悔。可是干下出卖、杀戮勾当的那些人向神父忏悔后,居然可以遗忘自己的恶行而心安理得,神父派佩感到自己担当的,其实是“下水道”的角色。他对布罗岱克说:“战争,那是一只扫荡世界的大手。那是平庸之辈春风得意的地方,是罪犯接受圣人光环的地方……你为不得不讲述那些人的滔天罪行而感到孤立无援,我为不得不原谅那样的罪行而感到孤立无援。”派佩认为,“另外那个人”如同镜子,照出了那些小镇居民的丑恶本相,可是,“所有的镜子都只能以破碎告终”。
小说结尾,布罗岱克写完了报告,可是镇长奥施威尔却将如实记录这次谋杀的报告塞进火炉。他警告布罗岱克:必须遗忘战争发生以来小镇居民的恶行,即便是出卖、谋杀、残害,“在所有的危险中,记忆的危险是最可怕的危险之一,你是不是记得太多了?”
布罗岱克报告所记录的小镇中的人,并非恶魔,只不过是农人、手工业者、护林人、店铺老板、小公务员,可是在战争发生以来的日子里,为了自身的生存,这些人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而且又集体谋杀了“照出”小镇居民丑恶本相的“另外那个人”。
就这样,《布罗岱克的报告》在二战的时代背景下剖析人性。那字里行间细诉的小镇居民的罪恶,足以与世人公认的纳粹集中营暴行并驾齐驱,成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大痛苦。然而对如此大痛,居然必须遗忘,因为“记忆的危险是最可怕的危险”。如实记录的报告就这样被塞进火炉——这,才是让人无法遗忘的剧痛。《布罗岱克的报告》作者的聚焦,由此鞭辟入里、发人深省。文学对人性的剖析,亦因此具有宏大历史的立体景深。
|